11 SEP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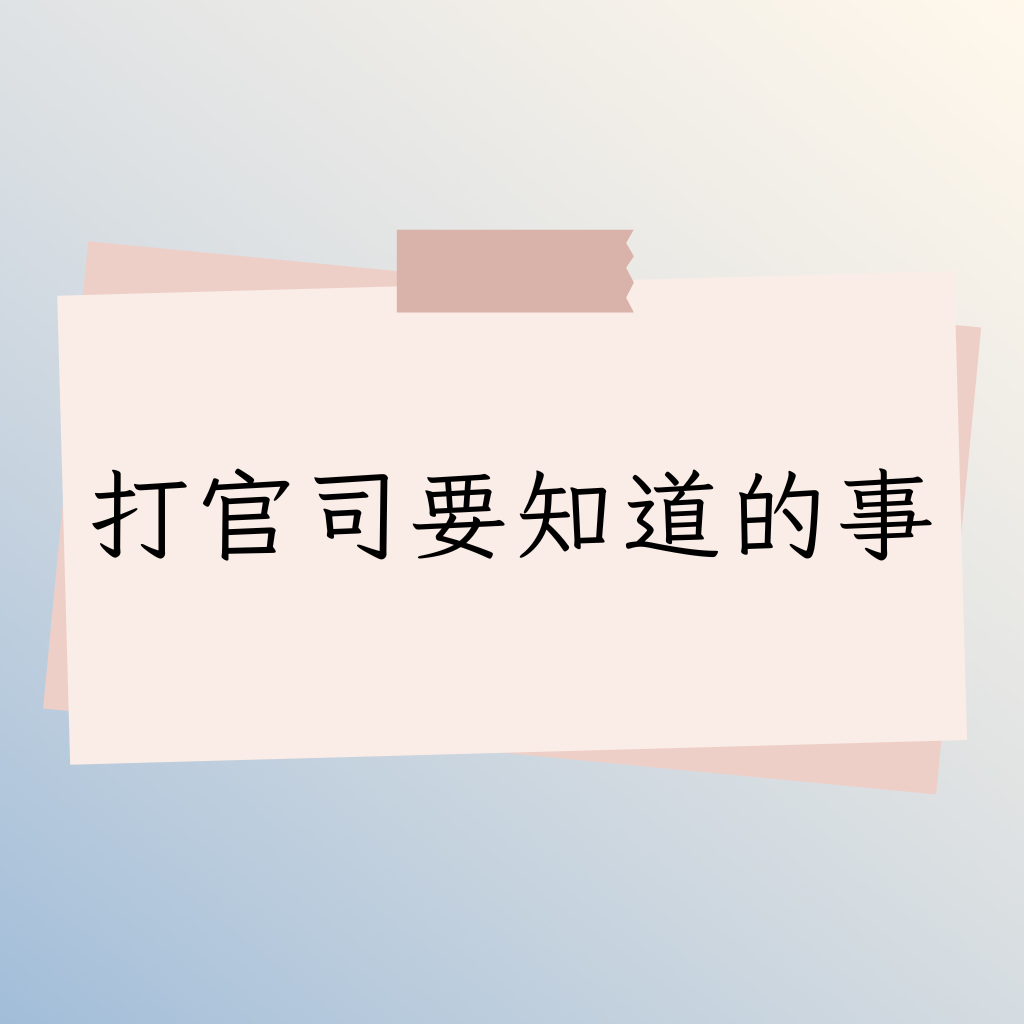
「您心中的公平正義,應該是什麼樣子?」
當事人尋求法律協助時,心中往往懷抱著對「公平正義」的殷切期盼。許多人認為,法律就是公平正義的化身,理應實現「殺人償命、以牙還牙」這類直觀的正義。然而,在多年的執業生涯中,我發現法律的運作遠比這複雜。它並非一套冰冷、絕對的道德準則,而更像是一部為了維護社會整體秩序、經過深思熟慮後產生的「折衷」產物。
每個人的成長背景、價值觀與所處立場各不相同,這也導致我們對「公平」的定義南轅北轍。您的公平,不見得是別人的公平;而法律,則必須在這些相互衝突的「公平」之間,尋找一個能讓社會最大多數人依循的平衡點。
本文將透過幾個常見的法律議題,包含刑事案件中的「認罪協商」、「自首減刑」,以及民事案件中的「監護權酌定」、「越界建築」與「遺產特留分」,帶您一窺法律制度背後,那些關於資源分配、利益衡量與人性現實的深層考量。理解這些,您將能更清晰地看懂法官的思維,並在面對法律問題時,做出更智慧、更務實的決策。
許多人認為,追求正義不應計較成本,應當「上窮碧落下黃泉」,不計代價地查明真相、嚴懲兇手。這份理想固然崇高,但在現實的司法體系中,「資源有限」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司法資源如同任何公共資源,必須被有效率地分配,才能處理龐雜的社會紛爭。因此,刑事司法程序中發展出一些看似「打折扣」,實則充滿制度善意的機制。
「認罪協商」常被誤解為被告與檢察官在菜市場討價還價,彷彿司法尊嚴蕩然無存。然而,這項制度的設計初衷,正是為了在有限的司法資源下,達到更有效率的犯罪追訴。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認罪協商是在被告認罪的前提下,與檢察官協商一個較輕的刑度。值得注意的是,此制度並非適用於所有案件,法律已明確排除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等重罪,以確保重大惡行不會被輕易「協商」掉。
認罪協商的核心價值在於「節省司法資源」。與其將大量時間與人力耗費在事實相對明確的案件上,不如透過協商快速終結程序,讓檢察官與法官能將精力集中在案情複雜、證據矛盾的重大案件上。
更深一層來看,認罪協商也是一種「風險管理」的工具。試想一個情境:檢察官手上證據不夠充分,案件判決有罪或無罪的機率各半。此時,若能透過認罪協商,至少能確保被告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裁,避免了因證據不足而完全脫罪的最壞結果。對被告而言,這也避免了若審判到底,可能面臨更重刑罰的不確定性風險。因此,這看似「喊價」的過程,實則是控辯雙方在訴訟風險與成本考量下的理性策略。
此外,臺灣的認罪協商制度之所以不如美國普遍,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已有「簡易判決處刑程序」能有效處理許多輕微案件,這也反映了不同法制在追求效率時,會發展出各自的配套措施。
「事情做了就是做了,為什麼自首就能減刑?」這也是許多人心中的疑問。法律給予自首者減刑的機會,並非認為其罪行因此變得比較輕微,而是出於更務實的立法考量:鼓勵犯罪者主動揭露犯行,以節省龐大的偵查成本。
首先,必須精準地理解法律上的「自首」。根據《刑法》第62條,自首必須是在「犯罪尚未被發覺」前,主動向有偵查權的機關(如警察、檢察官)陳述犯行並願意接受裁判。這與幾個相似但不同的概念有著天壤之別:
這四者的區別,正體現了法律的專業與精確。
更關鍵的是,2005年《刑法》修正時,將自首的規定從「減輕其刑」改為「得減輕其刑」。這個「得」字,賦予了法官裁量權,意義極為深遠。它意味著自首不再是換取減刑的「自動折扣券」,法官有權去審視被告自首背後的動機。他是真心悔悟,希望彌補錯誤?還是眼見法網恢恢、走投無路下的投機之舉?這項轉變讓法律的適用更具彈性與智慧,不再是僵化的公式,而是對人性的細膩洞察,也再次印證了法律判斷的複雜性。
相較於刑事案件,民事案件雖不直接涉及國家刑罰權,但同樣充滿了艱難的價值判斷。在民事領域,「公平」更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在各種合法卻相互衝突的權益之間,尋找一個最不壞的解決方案。
在離婚案件中,最令人揪心的莫過於子女監護權(法律上稱為「親權」)的歸屬。當父母雙方都是愛孩子的「好爸爸」、「好媽媽」時,法官該如何做出「公平」的判決?是一人一個孩子嗎?
這正是民眾與法律思維最大的分歧點。法律在此的核心原則,並非滿足父母對「公平」的感受,而是《民法》第1055條之1所揭示的最高指導原則——「子女之最佳利益」。法律明確指出,監護權是父母對子女的「責任與義務」,而非自身的「權利」。
因此,法官在判斷時,會像拼圖一樣,綜合考量極為繁多的因素,包括:子女的年齡、意願、主要照顧者是誰、父母的經濟能力、品行、居住環境、對教養的態度,甚至是否願意與另一方合作等。法官的目標不是讓父母感覺「公平」,而是為孩子建構一個最穩定、最有助於其身心發展的未來。從這個角度出發,「一人一個」看似公平,但若因此拆散手足,對孩子的成長可能造成傷害,反而不符合其最佳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的判斷標準也在演進。過去可能較偏重「幼年子女從母」的原則,但近年來更重視「主要照顧者原則」(由長期負責孩子日常起居的一方繼續照顧)與「繼續性原則」(盡量不改變孩子熟悉的生活環境)。此外,「友善父母原則」也日益重要,法官會觀察哪一方更願意保障並促進孩子與另一方家長的互動,因為與父母雙方都保持良好關係,才真正符合子女的長遠利益。
「律師,他家蓋到我的土地上,這不是侵占嗎?叫他拆掉,天經地義吧!」這是土地所有權人最直覺的反應。絕對的財產權保障,聽起來理所當然。然而,我國《民法》在處理「越界建築」時,卻做出了非常精巧的利益衡量。
根據《民法》第796條及第796條之1的規定,當鄰居蓋房子不小心(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蓋過界,如果拆除這越界的部分會嚴重損害建築物的整體結構與經濟價值時,法院可以權衡公共利益與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判決免予拆除。
這是否代表被越界的地主只能自認倒楣?當然不是。法律將地主的「物權」進行了轉換:原本「要求返還土地」的權利,轉變為「請求金錢補償」的權利。越界的一方必須支付償金,或以相當的價額購買被占用的土地。
這個制度完美體現了法律的「折衷」精神。立法者考量到,為了一點點無心之失的越界,就耗費鉅額成本拆除一棟價值不菲的建築物,對個人和整體社會經濟都是巨大的浪費。因此,法律選擇了一條兼顧雙方利益的道路:保障被侵害者獲得金錢賠償,同時也避免了不成比例的社會資源耗損。
當然,法律也要求權利人不能「睡著了」。如果地主在鄰居動工時就「知其越界而不即提出異議」,事後才想主張拆屋,其權利將會受到限制。這也提醒我們,維護自身權益必須及時。
「我的財產,想給誰就給誰,為什麼法律還要管?」這是許多被繼承人在規劃遺產時的共同心聲。然而,我國《民法》設有「特留分」制度,它就像一道法律上的安全防線,限制了個人處分遺產的絕對自由。
首先,我們需要區分兩個重要概念:「應繼分」與「特留分」。
特留分的設計,是基於社會政策的考量,避免因被繼承人的偏愛,導致某些繼承人(尤其是需要扶養的親屬)頓失依靠,生活陷入困境。它在個人的遺囑自由與繼承人的生存保障之間,取得了一個平衡點。
特留分的計算方式,是先算出「應繼分」,再依繼承人種類乘以特定比例。以下表格可供快速參考:
| 繼承人種類 | 與配偶共同繼承時之應繼分 | 特留分比例 | 最終特留分計算 |
|---|---|---|---|
| 直系血親卑親屬 | 與配偶均分 | 應繼分之 1/2 | 應繼分 ×1/2 |
| 父母 | 配偶得 1/2,父母均分另 1/2 | 應繼分之 1/2 | 應繼分 ×1/2 |
| 兄弟姊妹 | 配偶得 1/2,兄弟姊妹均分另 1/2 | 應繼分之 1/3 | 應繼分 ×1/3 |
| 祖父母 | 配偶得 2/3,祖父母均分另 1/3 | 應繼分之 1/3 | 應繼分 ×1/3 |
資料來源: 《民法》第1144條、第1223條
一個關鍵的重點是,特留分並非自動生效的權利。如果繼承人的特留分被侵害,他必須主動行使「扣減權」,向拿到較多遺產的人主張。並且,這個權利有時效限制,必須在知悉被侵害起的2年內,或自繼承開始起的10年內行使,逾期則可能喪失權利。
這也意味著,遺產規劃是一門充滿策略的專業領域。如何透過生前贈與、保險或信託等合法工具,在尊重被繼承人意願的同時,又能兼顧法律規定,正是專業律師能提供價值之所在。
從刑事司法的資源節約,到民事案件的利益衡量,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法律並非一把能斬斷所有紛爭的萬能寶劍。它更像一位經驗豐富的協調者,在各種相互拉扯的力量中,努力尋找一個可行的、能讓社會繼續運轉的平衡點。
認識到法律的局限性與其背後的折衷、權衡思維,並非是對法治的失望,而是一種法律上的成熟。當您理解法律為何如此規定,便能對訴訟結果有更合理的預期,避免因過高的期待而產生巨大的失落感。
更重要的是,這份理解能賦予您力量。它讓您在面對法律挑戰時,不再僅僅停留在「公不公平」的情緒中,而是能與您的律師一起,從更宏觀、更策略性的角度,分析利弊得失,制定出最符合您現實利益的行動方案。
在亮遠法律事務所,我們深信,真正的專業不僅是嫻熟法律條文,更是洞悉法律背後的現實邏輯。若您正身處法律的十字路口,我們願以這份深刻的理解與務實的態度,陪伴您撥開迷霧,找到最清晰的前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