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SEP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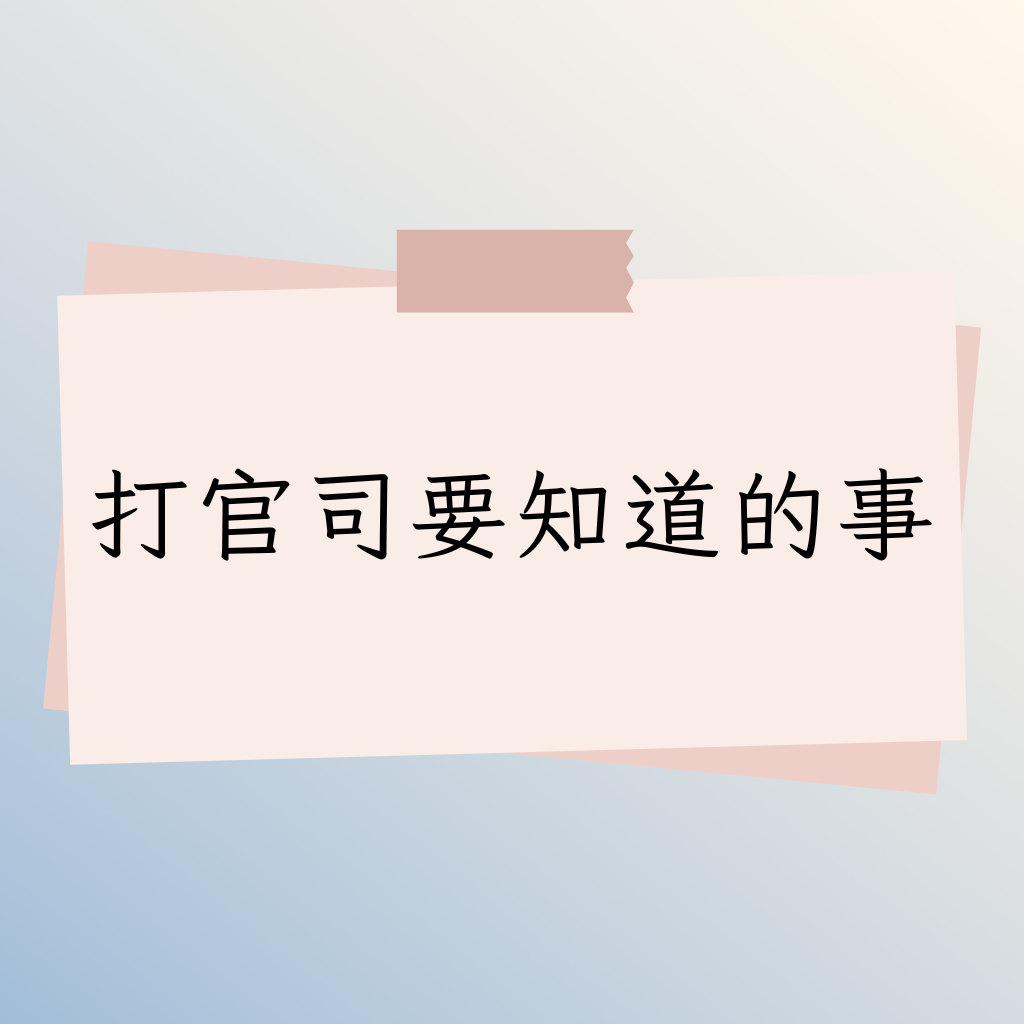
法律協商不是戰場:當「鷹派」遇上「鴿派」,律師教你如何談出最佳結果
談判,是人類社會互動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是國家間的貿易協定、企業間的商業合作,抑或是個人生活中的大小事,都離不開協商與溝通。在複雜的談判情境中,人們常會將參與者的姿態分為兩種類型:「鷹派」與「鴿派」。這兩種形象化的比喻,不僅能幫助大眾快速理解談判中的基本態度,更能為深入探討法律協商策略奠定基礎。
「鷹派」與「鴿派」的概念,最早廣泛應用於財經領域,尤其在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討論中屢見不鮮。所謂的「鷹派」(Hawk),通常指的是態度較為強硬的一方,他們傾向於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例如透過升息來控制通貨膨脹,以維護物價穩定為首要目標。相對地,「鴿派」(Dove) 則指態度較為溫和的一方,他們更傾向於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例如透過降息來刺激經濟成長,以促進就業和經濟發展為優先考量。
這種比喻之所以被廣泛採用,是因為它將複雜的經濟政策立場,轉化為大眾易於理解的形象化概念,有效降低了專業知識的門檻。透過這種直觀的對比,讀者能夠迅速掌握兩種截然不同的決策風格及其潛在影響,為後續在法律場景中的應用建立起清晰的認知框架。這對於希望透過白話內容讓潛在客戶認識並理解其風格的法律事務所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溝通策略。
「鷹派」與「鴿派」的分類方式,同樣適用於法律領域中的訴訟調解或商業協商場合。然而,法律協商與一般商務談判之間存在一個關鍵的差異:訴訟調解中,存在一個「法官作為第三方」的角色。這意味著,如果調解未能成功,案件最終將由法官進行審理。
法官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關心調解過程中的狀況,並可能將其列為心證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離婚訴訟和監護權爭議這類涉及高度情感與家庭關係的案件中。雖然調解過程中提出的方案不能直接作為最終判決的基礎,以確保當事人能夠自由地進行協商而不受拘束,但在許多案件中,法官對於調解狀態的關注,暗示了司法體系對於當事人透過合意解決糾紛的鼓勵。這也意味著,在法律協商中,單純的強硬姿態不僅可能激化與對方的矛盾,更可能在法官心中留下負面印象,進而間接影響後續訴訟的判斷。因此,律師在引導當事人進行調解時,不僅要考慮與對方的博弈,更需策略性地展現合理性與合作意願,為可能的訴訟階段預先鋪陳有利的司法印象。
以下表格將鷹派與鴿派思維在不同領域的特徵進行對比,以幫助讀者更清晰地理解其應用:
| 特徵/領域 | 鷹派 (Hawk) | 鴿派 (Dove) |
|---|---|---|
| 財經領域 | 強硬態度、升息、控制通膨 | 溫和態度、降息、刺激經濟 |
| 訴訟調解 | 強硬要求、不願妥協、追求最大利益、可能激化矛盾 | 願意溝通、適度讓步、尋求共識、可能促成和解 |
| 商業談判 | 嚴格審約、要求擔保、強調風險控管、可能導致交易破局 | 彈性協商、注重成交、追求合作機會、可能促成合作 |
| 潛在風險 | 談判破裂、錯失機會、激化矛盾、訴訟風險增加 | 可能讓步過多、權益受損 (若無策略引導) |
這份表格透過視覺化的方式,將鷹派與鴿派在不同情境下的表現、目標與潛在風險進行了系統性歸納。這不僅能讓讀者一目瞭然地比較兩種思維模式的差異,更能幫助他們快速掌握核心要點,從而提升對談判策略的理解深度。這種清晰的呈現方式,同時也展現了律師對於複雜議題的分析能力與專業判斷。
離婚協商,對於許多人而言,被視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前三複雜的協商或談判」之一。其複雜性不僅在於情感的糾葛,更在於其牽涉的法律議題之廣泛與細緻。
一份完整的離婚協議書,所牽涉的議題遠不止於「離婚本身」。它必須全面性地處理雙方未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子女的監護權歸屬、探視權與會面交往的具體安排(例如平日、週末、過年期間從除夕到初五、中秋、端午、清明等節日的分配,甚至包含長輩及小孩生日的約定),以及交接狀況的處理細節,如遲到應如何進行等。此外,夫妻財產的結算更是核心議題,這不僅涉及夫妻之間的債務釐清,還包括房產登記在誰名下、房貸是否有對方擔任保證人等複雜的財產分配問題。
這些細節的羅列,不僅突顯了離婚協商的龐雜性,更暗示了若在每個環節都採取極端「鷹派」立場的困難。當議題數量如此龐大且環環相扣時,若當事人或其律師在每個點上都堅持己見,不願做出任何讓步,將極易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最終無法簽署協議。這也凸顯了律師在協助客戶進行「取捨」和「聚焦」核心利益上的重要性,避免客戶因過度糾結於瑣碎細節而忽略了達成整體協議的大局。律師的專業價值在於引導客戶辨識其真正的優先順序,並在次要議題上展現彈性,以促成整體協議的達成,避免因小失大。
協商的本質,從來都不是一方全盤勝利,而是雙方在一定程度上的「折衷與妥協」。若在協商過程中,一方抱持著「什麼都想佔、什麼都想強勢」的心態,企圖成為「霸道總裁」,期待對方像「小貓咪」一樣完全聽從,那麼在現實的離婚協商中,這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往往,當事人必須在某些方面爭取權益,而在另一些方面則需要做出讓步。
在離婚協商中,鷹派思維的表現可能包括要求加入對自己極為有利的懲罰性條款,例如若對方遲到歸還小孩,需支付高達一百萬或兩百萬元的懲罰性違約金,或是要求撫養費加倍等。然而,問題的癥結在於,對方也可能同樣是鷹派。既然雙方已經走到離婚這一步,彼此之間往往已「沒有情面可言」。在缺乏情感基礎和信任的背景下,任何一方過度不合理的索求,都極可能被對方視為挑釁,而非合理的訴求,從而激化矛盾。這種「鷹派對鷹派」的局面,最終往往導致根本無法簽署協議,被迫走向耗時耗力的訴訟程序。
許多客戶在尋求律師協助時,常會抱持著「我找你就是要你夠強硬,捍衛我的權益,甚至把對方電到講不出話來」的期待。然而,這種理想化的預期與現實往往存在巨大落差。律師的專業價值,不僅在於法律知識的運用,更在於能夠洞察談判的實質,引導客戶跳脫情緒的泥淖,從現實和策略的角度評估這些過度「鷹派」要求的可行性與潛在反噬。事實上,「什麼都想拿,最後很有可能就什麼都拿不到」,這不僅是談判的真理,更是對客戶的警示。律師會協助客戶識別並聚焦於其真正的核心利益,例如小孩的監護權,並在非核心利益上做出策略性讓步,以換取主要目標的達成。這種務實且智慧的策略,反而更有可能促成協議,甚至獲得比曠日費時的訴訟更好的結果,例如透過協商可能拿到訴訟中難以爭取到的監護權。這才是真正為客戶實現整體最佳利益的途徑。
在商業世界中,談判同樣是日常運作的核心。企業內部不同部門之間,也經常上演著「鷹派」與「鴿派」的拉鋸戰,這尤其體現在法務單位與業務單位之間的意見衝突。
在公司內部,意見最矛盾的兩個單位,通常是傾向於「鷹派」的法務單位和傾向於「鴿派」或更具彈性的業務單位。法務單位的職責是從法律角度出發,仔細審查契約條款,提出對公司可能存在的疑慮,並要求增加擔保、設定懲罰性違約金等,以最大限度地確保對方履行合約,其核心目標是風險控管。
然而,業務單位則有著截然不同的考量。他們擔心法務單位過於嚴苛的條款會讓對方不願簽約,導致訂單無法成交,甚至影響公司的營運與市場佔有率。業務人員常會認為:「這樣搞,我們這一單不用接了,沒有人要跟我們做生意」。他們的首要目標是促成交易,追求商業機會的達成。
這種公司內部的衝突,實質上映射了客戶在面對法律建議時的兩難:究竟是應優先追求極致的法律保障,將風險降至最低,還是應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風險,以換取商業機會的實現?這也暗示了律師在提供建議時,不能僅僅從單一的法律風險角度出發,而必須深入理解客戶的整體商業目標、市場策略以及行業特性。一位成功的律師,不僅需精通法律條文,更需懂得如何將法律策略融入客戶的商業戰略之中,為客戶在法律保障與商業可行性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從而提供更具實用價值的解決方案。
在法律協商中,律師的角色絕非單純地扮演當事人的「打手」,盲目地追求強硬與勝利。相反地,律師的專業價值在於提供策略性指導,引導當事人釐清目標、管理風險,並在談判桌上找到最有利的平衡點。
律師的職責是從法律角度出發,盡力小心審查契約,並提出對當事人權益有充分保障的方法。然而,當事人必須理解,律師所提供的法律建議,本質上是為了提醒其潛在風險並提供保護措施,這「不代表你必須這麼強硬」。
若在協商中,每一個條款都要求對方百分之百履行,並堅持加上高額的懲罰性違約金條款,那麼對方很可能根本不願意簽約,甚至反過來要求己方也承擔類似的懲罰性違約金,最終將導致整個協商無法進行。協商的目標並非為了簽訂充滿危險或不切實際條款的協議,也不是完全不計較任何細節,而是在風險控制與實際可行性之間找到一個務實的平衡點。
許多客戶對律師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認為律師越強硬,越能「捍衛權益,甚至把對方電到講不出話來」。然而,這種觀念可能導致協商破裂,錯失達成協議的機會。律師的真正價值在於提供全面的「策略性」指導,幫助客戶認識到談判的成功往往源於靈活性而非僵硬。透過理解對方的底線並適時調整策略,律師能夠引導客戶避免因過度強硬而導致談判陷入僵局,最終促成有效且對客戶有利的協議。
成功的協商,其關鍵在於當事人必須「想清楚自己『最在乎』或『最重要』的是什麼」。例如,在商業契約中,交貨日期可能比其他次要條款更為重要;而在離婚協商中,小孩的監護權可能遠比財產分配的某些細節更具優先性。
律師在此階段的職責,便是協助客戶「去蕪存菁」,將談判的重心專注於最關鍵的目標。如果當事人試圖「什麼都想拿」,例如同時要求日期、價格、擔保、以及其他所有優惠,這種過度索求的姿態將會讓對方不願繼續談判,最終可能導致交易破局或協議無法簽署。律師會引導客戶進行「利益排序」和「目標聚焦」,將談判資源和精力集中在核心目標上,並在次要目標上展現彈性或進行策略性讓步。這種策略性聚焦,能有效提高談判成功率,避免因貪小失大而導致整體失敗。
在法律實務中,並非契約寫得越詳細、對自己越有利,事情就一定能辦成。有時,律師甚至會故意將某些條款寫得「稍微模糊」,以保留日後若有爭議時的處理彈性與空間。這是因為文字本身無法涵蓋所有可能發生的情形,無論契約條款如何仔細,都無法百分之百保證未來不會有爭議,律師也無法擔保協議書能完全避免所有爭議。
契約的重點在於「避免最危險或最大的風險發生」,而非追求零風險的絕對完美。這種「故意模糊」的策略,挑戰了客戶對於「契約越詳細越好」的普遍認知,顯示了律師在處理複雜法律事務時的靈活性和前瞻性。律師不僅關注當下條款的嚴謹性,更會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變數和爭議解決的空間。這也間接說明了律師的專業價值在於「風險管理」而非「風險消除」,能夠為客戶提供更具彈性和實用性的法律文件。
此外,律師坦誠無法擔保協議書百分之百沒有爭議,這是一個重要的「預期管理」環節。它幫助客戶建立務實的預期,理解法律服務的邊界和現實世界的複雜性,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失望和誤解。這種透明的溝通,反而能建立更深層次的信任,讓客戶理解律師的專業是基於現實風險評估和管理,而非提供虛假的安全感,進一步強化律師作為務實、專業顧問的形象。
在法律協商的過程中,當事人與其律師所採取的姿態,將直接影響談判的走向與最終結果。如何在強硬與溫和之間取得平衡,是達成協議的關鍵。
在進行取捨時,當事人必須清晰地考慮「什麼對自己最重要」,這是制定談判策略的基石。在協商過程中,不妨「適度地釋放一些善意或退讓」。這種退讓並非軟弱,而是一種預想中的策略性讓步。例如,在商業談判中,可以一開始將價格拉高,之後再適度退讓,為談判留下彈性和空間。這種策略性讓步,是高明的談判技巧,它不僅能有效打破僵局,促成協議,同時也能讓對方感受到己方的誠意,為未來的合作或關係緩和留下空間。律師會引導客戶在談判前,就預設好哪些是核心利益不可退讓,哪些是次要利益可以作為讓步籌碼,從而提供更全面、更智慧的解決方案。
總而言之,在談判時,不應認為「越強硬越好」,因為一味地強硬往往會導致僵局,甚至談判破裂,最終可能什麼都拿不到。因此,無論當事人是傾向於「鷹派」還是「鴿派」思維,最好的策略是能夠「折衷一點,不要要求一定要事事爭贏」。
法律協商的最終目標是讓談判或調解成功。一個成功的協商結果,往往比曠日費時、耗費巨大心力與金錢的訴訟更能符合當事人的最大利益。律師的專業價值,不僅在於精通法律條文,更在於對談判藝術和人性的深刻理解。透過引導客戶採取「鷹鴿並濟」的策略,律師能夠幫助客戶在複雜的法律糾紛中,找到最務實且有利的解決方案,實現超越預期的價值。這也確立了律師作為務實、專業且值得信賴的法律顧問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