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SEP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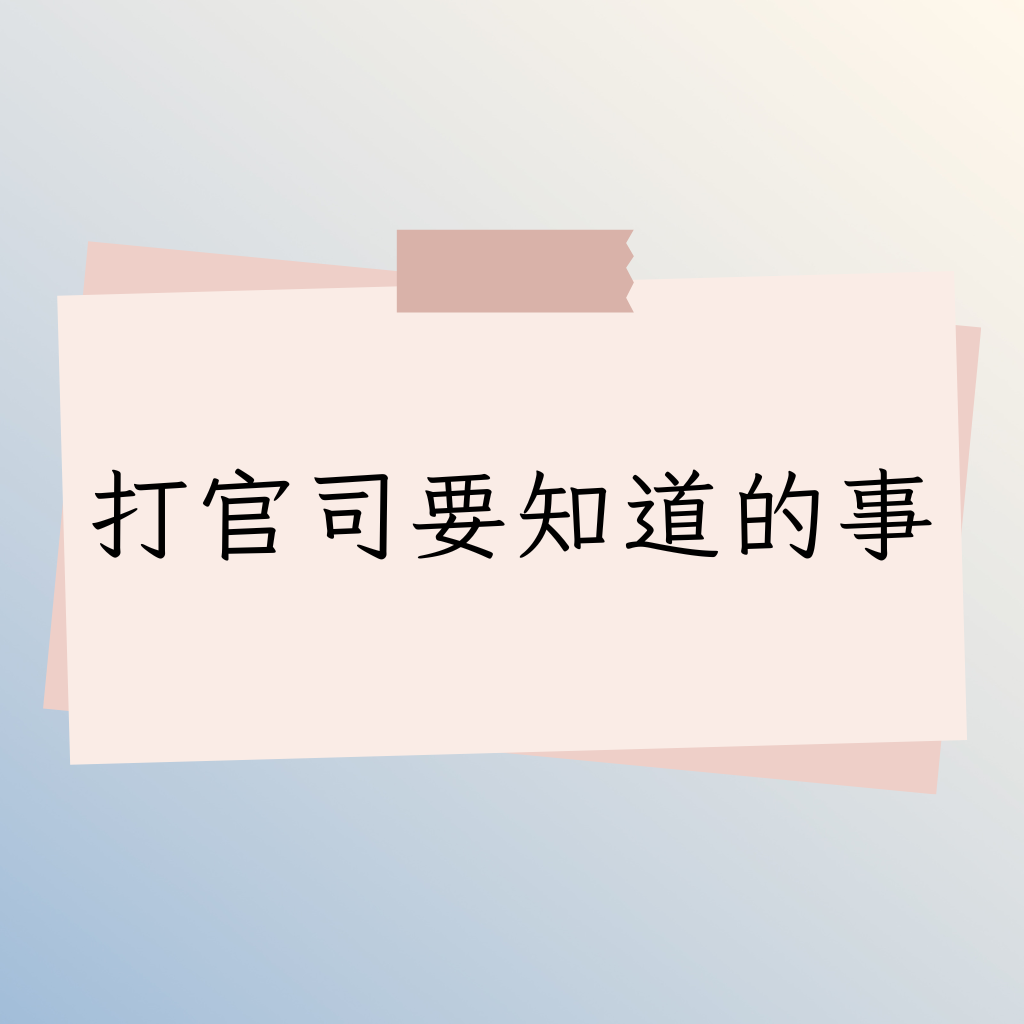
許多當事人在法庭上,總會急切地想向法官傾訴自己所承受的痛苦與委屈。他們可能會用「無法忍受」、「極其惡劣」、「持續不斷」等詞語,鉅細靡遺地描述對方的行為對自己造成的傷害,卻往往只換來法官冷靜的追問,甚至是要求提出更具體的證明。這種溝通上的落差,常讓當事人感到挫折與不解:「我說的都是真的,為什麼法官好像不相信我?」
這份挫折感的根源,在於訴訟攻防中一個極其重要卻常被忽略的核心原則:法律重視的是「名詞」,而非「形容詞」。
這裡的「形容詞」,指的是您主觀的感受、情緒性的描述或個人詮釋,例如「對方態度很差」、「噪音非常吵」、「他這個人很不老實」。而「名詞」,則是指那些客觀、可供驗證的事實與證據,例如一份對方的「刑事判決紀錄」、一張明確記載分貝數的「噪音檢測報告」、或是一紙詳列傷害部位的「診斷證明書」。
本文將深入解析,為何將您的主張從充滿情緒的「形容詞」,轉化為有憑有據的「名詞」,是說服司法系統、贏得訴訟的致勝關鍵。這不僅是一種說話技巧,更是理解整個司法運作的根本思維轉變。
在法庭上,許多看似強烈的形容詞,其實是空洞且無效的。因為它們缺乏一個客觀的衡量標準,法官無法單憑這些詞語來判斷事實的全貌與嚴重程度。
(一) 人身傷害:「非常嚴重」有多嚴重?
在車禍求償案件中,當事人常向法官陳述自己的傷勢「非常嚴重」。但這句話本身並未提供任何有價值的資訊。法官無法從「非常嚴重」這四個字,判斷您是輕微的擦挫傷、需要縫合的撕裂傷、骨折,還是將造成永久性失能的重傷害。每一個傷害等級所對應的賠償金額、精神慰撫金、以及對生活的影響程度,都有天壤之別。若沒有客觀證據支持,您的「嚴重」就只是一種主觀感受,無法成為判決的依據。
(二) 家庭暴力:「很常家暴」是多久一次?
在離婚或家暴相關訴訟中,主張「對方很常對我施暴」同樣會面臨挑戰。法官心中的疑問是:「很常」的頻率究竟為何?是五年發生一次,還是一週發生數次?這兩者在法律上所代表的婚姻破裂程度、施暴的持續性與急迫性,截然不同。法律需要評估的是一種可證實的行為模式,而非模糊的時間概念。若無法將「很常」具體化,您的主張力道將會大打折扣。
(三) 環境侵權:噪音「很吵」、空污「很臭」的法律意義為何?
對於噪音、惡臭等侵權行為,當事人常抱怨鄰居「吵死人了」或工廠排放的廢氣「臭到無法生活」。然而,每個人對於聲音與氣味的耐受度天差地別。您認為刺耳的聲響,在他人耳中可能只是背景音;您覺得難聞的氣味,或許他人無感。法律作為社會共同的行為準則,不能建立在如此主觀且浮動的個人感受之上。因此,單純形容「很吵」、「很臭」,在法律上幾乎沒有意義,法官也無從判斷侵權行為是否已逾越一般人所能容忍的界線。
要克服形容詞的無力,就必須學會使用「名詞」——也就是客觀證據——來陳述事實。這些具體的證據,能將您的主觀感受轉化為法官可以採納的客觀事實。
(一) 從診斷證明書到環保局罰單:將傷害與侵權「量化」
讓我們重新檢視前述的例子,並用「名詞」來取代「形容詞」:
這些「名詞」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們來自中立的第三方(如醫院、政府機關),具備客觀性,能讓法官在一個明確的標準下進行判斷。
(二) 從過往判決到卷內物證:用事實攻擊對方的可信度
當您想讓法官懷疑對方或其證人的說詞時,同樣應避免使用「他這個人品格很差」、「他說謊不眨眼」等形容詞。這些只是人身攻擊,不具法律效力。
更專業且有效的方式,是提出客觀的「名詞」證據來彈劾其證詞的可信度。例如:
為了讓您更清晰地理解兩者差異,以下表格整理了常見的無效主張與有效的證據策略:
表一、「形容詞」主張 vs. 「名詞」證據:法庭說服力對比
| 無效的「形容詞」主張 | 有效的「名詞」證據 |
|---|---|
| 我的車禍傷勢非常嚴重。 | 提出載明「X光顯示右腿粉碎性骨折,需進行手術並植入鋼釘」的診斷證明書。 |
| 他經常對我施暴,我無法忍受。 | 提出過去一年內的五張驗傷單、顯示瘀傷的照片,以及保護令聲請紀錄。 |
| 鄰居的噪音吵死人,讓我精神衰弱。 | 提出環保局噪音超標的罰單、有時間戳記的錄音/錄影檔,以及分貝計測量紀錄。 |
| 對方這個人品格很差,他說的話都不能信。 | 提出對方曾因偽證罪或詐欺罪遭判刑的前科紀錄。 |
| 證人說謊,他講話眼神閃爍、結結巴巴。 | 指出證人陳述與卷宗內的客觀物證(如監視器畫面、合約條款)存在明確矛盾。 |
理解為何司法系統如此依賴「名詞」,需要我們換位思考,從法官與檢察官的角度看待整個訴訟程序。這不僅是規則要求,更是司法體系維持其公正性與可信度的基石。
(一) 判決書的基石:法官如何建構經得起上訴考驗的心證?
法官判案,最終必須產出一份詳盡的「判決書」。這份文書的核心,在於交代法官「心證」的形成過程——也就是他為何相信某一方、採納哪些證據、並最終做出勝敗的判斷。
法官的心證並非憑空得來的「直覺」或「感受」。它必須建立在法庭上呈現的各種人證、物證、書證之上。更重要的是,一審判決並非最終結果,敗訴方很可能會提起上訴。屆時,二審法院的法官將會逐一檢視一審判決書的理由是否充分、邏輯是否嚴謹、證據採納是否合法。
試想,如果一位法官在判決書上寫道:「因原告看起來十分痛苦,本院採信其說法」,這樣的判決理由在二審幾乎不可能站得住腳。相反地,如果理由是:「依據A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證實原告受有…等傷害,故其請求…為有理由」,這就是一個建立在客觀證據(名詞)之上、經得起考驗的判決。因此,法官在審理時要求您提出客觀證據,正是在為一份嚴謹、可供檢驗的判決書打下基礎。
(二) 起訴書的門檻:檢察官為何需要證據清單才能發動追訴?
同樣的邏輯也適用於刑事案件的偵查階段。當您作為告訴人,希望檢察官起訴被告時,您不能只說「我感覺就是他做的」。檢察官若要起訴一個人,必須製作一份「起訴書」,並附上詳盡的「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
這份起訴書的功能,是要說服法官「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進行審判的必要」。如果檢察官手中沒有足夠的客觀證據(例如:監視器畫面、指紋鑑定、金流紀錄、證人證詞),僅憑告訴人的指控或形容,是無法跨過起訴門檻的。缺乏「名詞」證據,檢察官就沒有發動追訴的武器,案件最終只會以不起訴處分告終。
總結來說,一場訴訟的成敗,往往不在於誰的聲音比較大、誰的形容詞比較華麗,而在於誰能提出更堅實、更客觀的「名詞」證據。
您在事件中所感受到的委屈與痛苦都是真實的,但法律有其獨特的溝通語言——那就是「證明」的語言。您的任務,就是將內心的感受,轉化為法庭能夠理解並採納的客觀事實。停止空泛的形容,開始有策略地蒐集、整理並提出能夠支持您主張的具體證據。
當然,從主觀的經歷中梳理出客觀的法律證據,是一項專業且複雜的工作。如果您正深陷法律爭議,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將是確保您的真實主張,能以最有力的方式呈現在法庭之上,進而爭取對您最有利結果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