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JUN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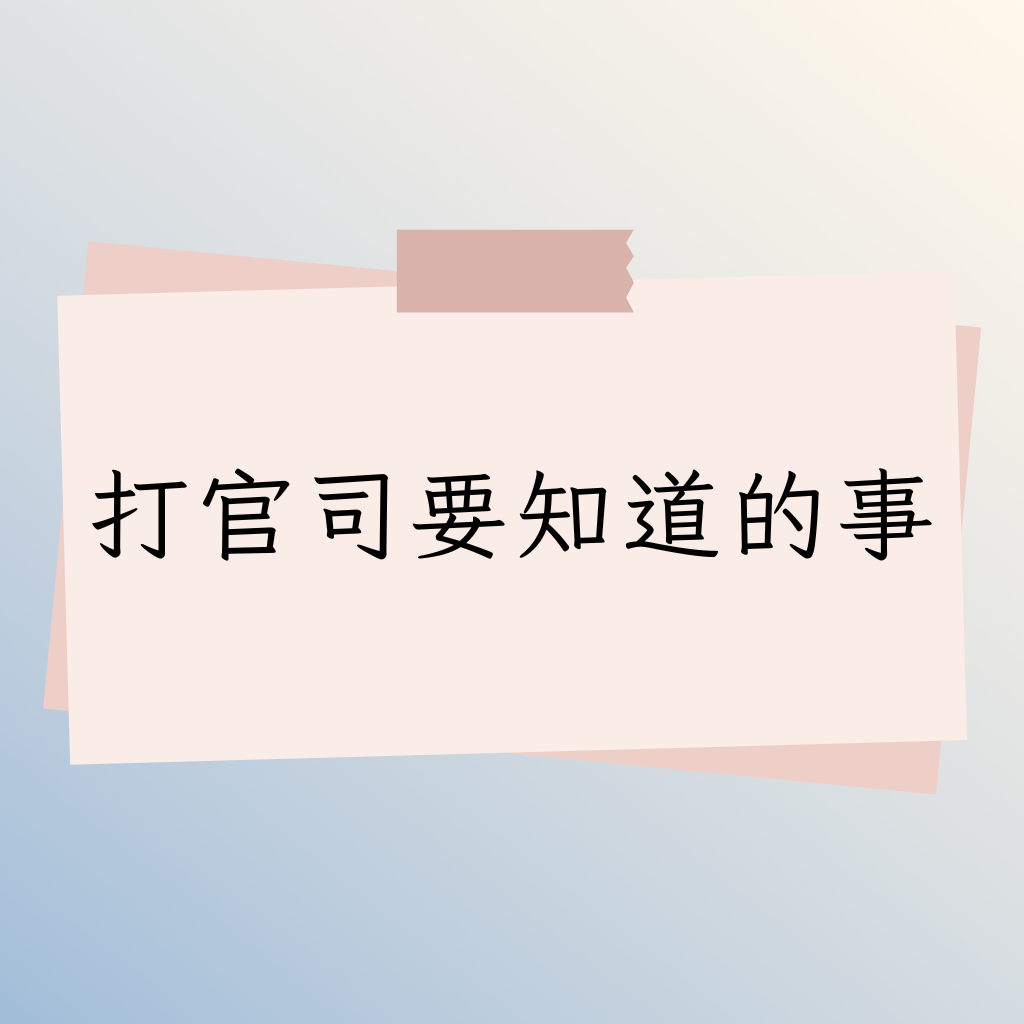
許多民眾對法庭的印象,往往來自於美國電影或影集中的激烈言詞交鋒,特別是律師詰問證人時的緊張橋段,例如近期廣受關注的強尼戴普與安柏赫德的官司,其法庭直播更讓大眾對美國式的交互詰問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這些戲劇化的呈現與台灣法庭的實際運作是否存在差異?「交互詰問」這個法律術語,在台灣的司法實務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
在美國法庭電影或影集中,交互詰問往往是劇情的高潮。我們常看到律師咄咄逼人地向證人提出一連串問題,證人可能因此啞口無言,甚至在律師巧妙的詰問下,一步步落入陷阱而不自知,最終情緒崩潰或吐露驚人真相。這些情節充滿戲劇張力,確實引人入勝。
儘管電影有所誇大,但交互詰問在美國的對抗式訴訟制度中,確實是發現真實及進行法律攻防的關鍵程序。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雙方律師對證人的提問,來檢驗證人證詞的真實性與完整性。詰問方律師會試圖從證人口中引導出對己方有利的事實,同時削弱或反駁對己方不利的證詞,甚至凸顯其矛盾之處,以說服作為事實認定者的陪審團。在此過程中,法官的角色相對被動,主要負責主持程序、裁決異議,較少主動介入詰問證人 。這種以陪審團為核心的制度設計,深刻影響了美國交互詰問的風格與策略,律師的表現往往更具說服性與敘事性,目標是爭取陪審團的認同。
(一) 制度的引進與目的
台灣的法庭,特別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確實也設有「交互詰問」制度,有時亦稱「交叉詰問」。此制度於民國92年9月1日全面施行,是我國刑事法庭活動的重大變革之一。其目的在於強化當事人進行主義色彩,讓檢察官、被告或其辯護律師等訴訟當事人,能直接對證人進行詰問,藉此呈現對己方有利的陳述,或挑戰對己方不利的證詞,從而協助法院發現真實 。台灣引進交互詰問制度,是參考了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其法制對台灣影響深遠 5)採納對抗制元素以提升審判透明度及當事人參與度的趨勢,逐步從傳統的職權主義模式進行調整。
(二) 詰問的進行順序:主詰問、反詰問、覆主詰問、覆反詰問
台灣刑事訴訟的交互詰問,依循特定的順序進行,主要分為四個階段:
1.主詰問: 由聲請傳喚該證人的一方先行詰問。其目的在於讓證人就待證事項及其關聯事項作證,建立起支持己方主張的事實基礎。詰問方應清楚意識待證事項,避免偏離主題 。
2.反詰問: 由對造當事人進行詰問。其目的在於對主詰問所呈現的事項及證人證詞的證明力提出質疑,揭露矛盾、不實之處,或引出對己方有利的證言。這往往是法庭劇中「問倒」證人的精彩環節。
3.覆主詰問: 再由聲請傳喚證人的一方,針對反詰問所引發的疑問進行澄清或解釋,以鞏固己方立場。
4.覆反詰問: 最後再由對造當事人,針對覆主詰問所顯現的證據證明力之必要事項進行詰問。
原則上,每一方都有兩輪詰問機會,透過這樣輪流詰問的方式,使證人的證詞在法庭上得到充分的檢驗。這種結構化的詰問順序及對各階段詰問範圍的限制,確保了程序的公平與效率,避免詰問漫無邊際。
(三) 詰問的主體與對象:誰來問?誰被問?
在刑事訴訟中,案件的當事人包括檢察官、被告或律師可以提出詰問。而被詰問的對象,則是依法傳喚到庭的證人或鑑定人。這種角色的明確劃分,是確保對抗式詰問程序得以有序進行的基礎。
(一) 當事人原則上不作證:與美國的顯著差異
在台灣的民事訴訟中,與美國(如前述強尼戴普案中,雙方當事人都親自上證人席接受詰問)有一個顯著的不同點:民事案件的當事人(原告、被告)原則上並不會像證人一樣,就其自身案件的事實宣誓作證。其理由在於,當事人本身就案件的利害關係,其陳述多被視為一種主張或辯解,而非中立客觀的證言。法院通常期望透過其他不具直接利害關係的證人、書證或物證來釐清事實。
(二) 「當事人詢問」制度的補充性質
雖然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原則上不以證人身分作證,但民事訴訟法中設有「當事人詢問」的制度。這並非讓當事人等同於證人,而是在法院認為確有必要,且已窮盡其他調查方式仍無法釐清案情,而當事人本身又掌握關鍵資訊時,才會發動的一種補充性程序。實務上,法院對於發動當事人詢問的態度相對保守,視其為釐清真相的輔助手段,而非主要的證據調查方式。
(三) 民事訴訟中證人詢問的規則與限制
台灣的民事訴訟雖然不像刑事訴訟那樣,對交互詰問的四個階段有著極其詳盡的成文規範,但這並不代表民事法庭上的證人詢問毫無章法。根據「民事訴訟集中審理證人訊問、發問參考要點」,民事訴訟中的證人詢問仍有一定的規則。通常,由聲請該人證的當事人先發問,再由對造當事人發問,之後聲請方可再發問。法官在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有權控制詰問的進行,並可限制或禁止不當的發問,例如與待證事實無關、重複、誘導、威嚇或涉及臆測性的問題等 。這顯示民事程序雖不如刑事程序對交互詰問有僵硬的四階段劃分,但仍透過法官的指揮與相關指引,確保證人詢問的有序與公正。
(一) 說服對象:法官 vs. 陪審團
在台灣,無論是刑事或民事訴訟,甚至在引進國民法官制度後,訴訟攻防最終要說服的對象,主要是職業法官(以及在特定案件中,與職業法官共同審判的國民法官)。相較之下,在美國設有陪審團的案件中,律師交互詰問的主要目標是說服由一般公民組成的陪審團。說服受過專業法律訓練的法官,與說服來自各行各業的陪審團,其策略與方法必然有所不同。前者可能更側重嚴謹的法律邏輯與證據分析,後者則可能更需要清晰易懂的敘事與情感連結。
(二) 法官的角色:職權調查色彩 vs. 中立聽審
傳統上,台灣的法官在審判中扮演較為主動的角色,帶有一定的「職權色彩」。即使在當事人進行交互詰問後,如果法官認為某些事實仍有未明之處,可以主動介入補充訊問。這與台灣深受大陸法系(特別是德國與日本法制)影響有關,法官對於真實發現負有一定責任 。而在美國的陪審團審判中,法官的角色更像是一位中立的裁判,主要負責維持法庭秩序、裁決法律爭議,較少主動對證人進行深入詰問 。
(三) 卷證資料的掌握:開庭前法官是否看卷
在台灣傳統的刑事訴訟(以及多數民事訴訟)中,法官在開庭審理前,通常已經閱覽過案件的全部卷證資料(稱為「卷證併送」)。這使得法官在開庭時對案情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相對地,美國的陪審團成員在審判開始前對案情一無所知,所有資訊都必須在法庭上透過證據逐一呈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自民國112年1月1日施行《國民法官法》後,在適用該法的特定重大刑事案件中,引進了「卷證不併送」原則(或稱「起訴狀一本主義」)。在此制度下,檢察官起訴時僅提交起訴書給法院,卷宗及證物不一併送交,因此職業法官與國民法官在審判前均無法接觸詳細卷證內容。這一變革使得法庭上的證據呈現與交互詰問,成為法官(含國民法官)首次且主要接觸案件細節的途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意味著台灣在特定案件類型上,也開始採納類似美國陪審團審判中「法官白紙」的模式。
交互詰問,無論是在台灣的刑事或民事訴訟中,都是一項旨在發現案件真實、保障當事人權益的重要法律程序。雖然其運作方式與電影中的戲劇化呈現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精神——透過對證人的提問與反駁,來檢驗證據、釐清事實——始終不變。對一般民眾而言,初步了解這項制度的樣貌與原則,有助於在不幸捲入法律紛爭時,能對法庭活動有更清晰的掌握。
然而,法庭程序畢竟錯綜複雜,尤其交互詰問涉及諸多法律規定、證據法則與訴訟技巧,非專業人士難以完全駕馭。從證人的選擇、詰問的策略、風險的評估,到面對國民法官制度的新挑戰,每一步都需要深厚的法律素養與實務經驗。因此,若您不幸面臨法律問題,或即將走上法庭,尋求專業律師的協助至關重要。一位經驗豐富的律師,不僅能為您分析案情、制定訴訟策略,更能在法庭上為您進行有效的詰問與辯護,在複雜的法律迷宮中,成為您最堅實的後盾,全力維護您的合法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