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JUL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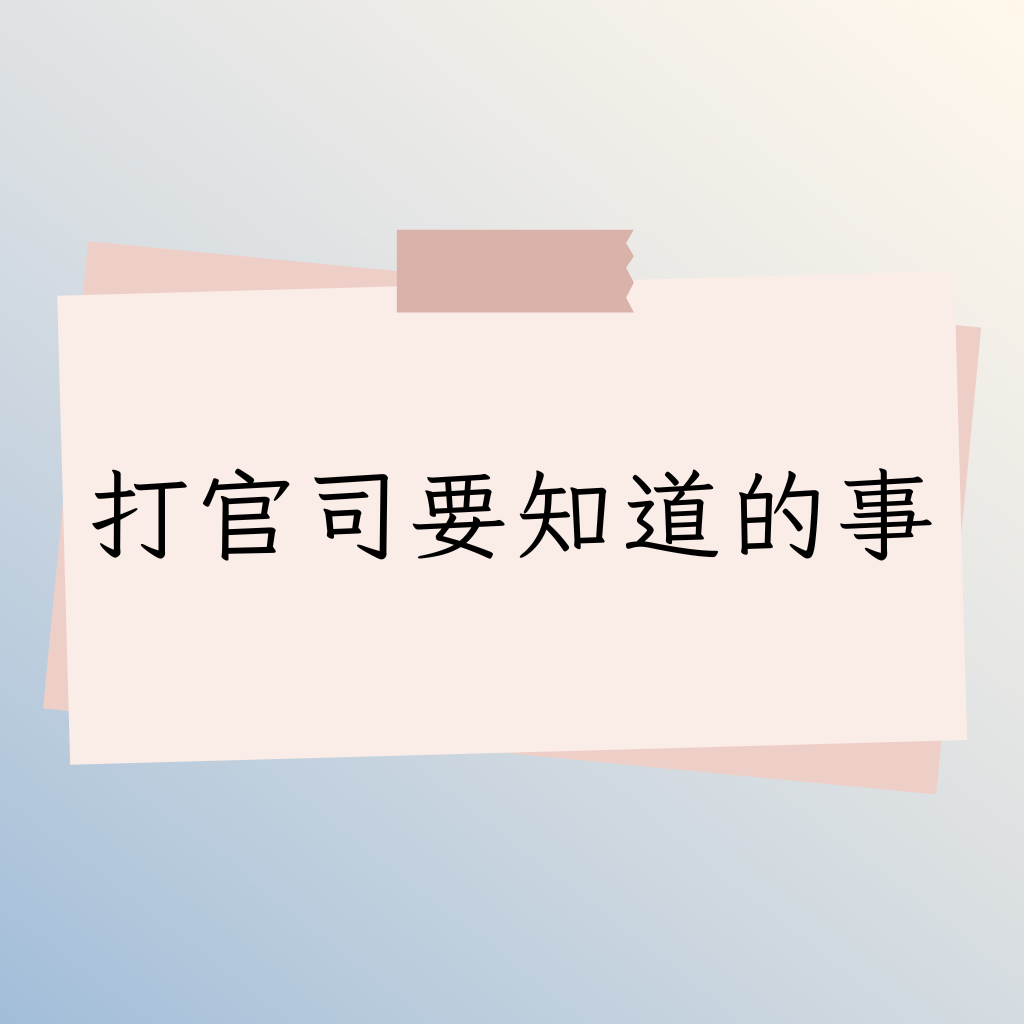
您是否曾經歷過這樣的場景?無論是在家庭聚會、朋友餐敘,還是在網路論壇上,一場關於政治、社會議題或公共政策的討論,最終演變成一場沒有交集、各說各話的爭執。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是對的,試圖說服對方,卻只換來更多的對立與情緒。為什麼有些對話,註定無法達成共識?
身為律師,在處理案件的過程中,我時常觀察到不同專業領域的人們,擁有截然不同的思維模式。醫師面對病患,必須在有限的資訊中,迅速做出診斷並規劃治療;工程師面對專案,需要用系統性的邏輯,確保建築或程式的穩定與安全。這些思維模式沒有高下之分,它們都是為了有效解決特定領域的問題而演化出的最佳路徑。
而法律人的思維,尤其是在處理訴訟時,也有一套獨特的運作方式。我們的工作,很多時候是在處理人與人之間的「爭議」。這些爭議五花八門,有些看似單純,有些則錯綜複雜。長年的經驗讓我體認到,許多無效爭執的根源,在於人們混淆了兩個基本卻至關重要的概念。這篇文章,我想與您分享這個核心的律師思維,它不僅是我們分析案件的起點,更是一個能幫助您在訴訟與日常生活中,看得更清晰、溝通更有效的強大工具。這個核心,就是學會區分:您們爭執的,究竟是「事實」,還是「觀點」?
在進入任何一場爭論或法律攻防之前,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就是準確地為爭議定性。如果連爭執的標的都模糊不清,後續所有的努力都可能徒勞無功。
所謂的「事實」,指的是一個客觀存在、可以被證明其真偽的陳述。它的核心特質是「可驗證性」。無論您喜不喜歡、相不相信,事實本身有其獨立於個人意志的標準答案。
舉例來說,「中華民國刑法目前仍然保有死刑條文。」這是一個關於「事實」的陳述。我們可以透過查閱《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等相關法條來驗證其真偽。答案是肯定的,法條白紙黑字地存在。因此,如果有人主張「台灣現在已經沒有死刑了」,這在事實層面上是錯誤的。在事實的領域裡,沒有模糊地帶,只有對與錯、真與假。
相較之下,「觀點」則是一個主觀的陳述,它反映的是個人的信念、價值觀、感受或判斷。觀點的核心特質是「主觀性」,它沒有、也不需要有標準答案。
讓我們延續剛才的例子:「我認為台灣應該要廢除死刑。」這就是一個典型的「觀點」。同樣地,「我認為台灣應該要維持死刑。」這也是一個觀點。這兩種看法,背後可能根植於對生命權的不同詮釋、對社會正義的多元想像、個人的宗教信仰,或是對犯罪嚇阻效果的不同評估。
您無法用「對」或「錯」來評價一個觀點。您可以贊同或反對,可以提出您的理由去說服對方,但您無法像驗證法條一樣,去「證明」哪一方的觀點才是唯一正確的。因為觀點之爭,本質上是價值體系之爭。
這個區分,不僅是邏輯思辨的練習,更是法律實務中至關重要的第一道程序。它決定了一位律師在接到案件後,將採取截然不同的訴訟策略與準備方向。
在法庭這個高壓的競技場上,「事實」與「觀點」的區分,決定了整個訴訟的主軸。律師與法官的工作,正是在這兩種類型的爭議中,尋找最接近正義的解答。
許多法律案件的核心,確實是「事實之爭」。這類案件的關鍵問題通常是:「這件事到底有沒有發生?」
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檢察官指控被告殺人或販毒。此時,法庭上下的所有努力,都圍繞著一個核心事實:被告究竟「有沒有」做這件事?檢察官必須提出人證、物證、科學鑑定報告等「證據」,來建構一個被告犯罪的完整事實圖像。而被告的律師,則會致力於挑戰這些證據的真實性與可信度,或者提出反證,來證明「事實並非如此」。
在民事案件中也是如此。例如,原告主張被告欠錢不還,爭議的核心事實就是「被告是否真的有借錢?」、「借款契約是否存在?」、「款項是否已經交付?」律師在這類案件中的首要任務,就是扮演一位事實的調查者與建構者,透過蒐集並組織證據,向法官呈現一個對我方當事人最有利、且最經得起檢驗的「事實版本」。在事實之爭的戰場上,「證據」就是唯一的武器與王牌。
然而,法律要處理的,並非全都是非黑即白的事實問題。有相當一部分的案件,其本質更接近於「觀點之爭」或「價值權衡」。在這些案件中,法官的角色不再僅僅是事實的發現者,更是一位權衡利弊得失、做出「最佳選擇」的決策者。
(一) 子女監護權的歸屬:一場關於「最佳利益」的價值權衡
離婚案件中的子女監護權(親權)歸屬,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當父母雙方都爭取孩子的監護權時,法官要判斷的,並不是「誰對誰錯」或「誰真誰假」。很多時候,父母雙方都是愛孩子的,也都能提出各自的優勢:一方可能經濟條件較好,能提供優渥的物質環境;另一方可能與孩子關係更親密,能給予更多的陪伴與情感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給予法官的指導原則是抽象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但什麼是「最佳利益」?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價值判斷的「觀點」問題。法官必須像一位經驗豐富的決策者,綜合考量父母的經濟狀況、職業、品行、與子女的互動情形、支持系統(有無後援長輩),甚至是雙方的健康狀況等數十個變數,最終做出一個他「認為」對孩子成長最有利的決定。這個決定,並非事實的裁決,而是一個在兩難中,經過深思熟慮的「觀點取捨」。
(二) 共有物分割:如何在「公平」與「經濟價值」間尋找平衡點?
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分割共有物」訴訟。例如,兄弟姊妹數人共同繼承了一塊土地,但彼此對於如何利用無法達成共識,只好訴諸法院請求分割。
此時,爭議的核心也不再是事實問題。每個人都想分到最有價值的部分,例如臨大馬路、地形方正的「黃金地段」。但「公平」該如何定義?是單純地將土地面積做等面積的幾何分割嗎?但這樣可能導致某些人分到價值低落的畸零地或山坡地。還是應該以「分割後總價值最大化」為目標,即便面積大小不一?或者,是否應該將整塊土地變價拍賣,大家直接均分現金?
這三種分割方式,都可能被主張為「公平」,但它們背後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點」。一種觀點重視形式上的平等,一種重視實質上的經濟效益,另一種則追求變現的便利性。不同的法官,可能基於對土地使用效益或對共有人需求的理解,而採納不同的分割方案。
理解了上述區別後,您就能更深刻地體會到,一位優秀律師在「觀點之爭」的案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當案件的核心是價值權衡而非事實真偽時,律師的工作不再只是舉證。我們的核心任務,是「為法官提供一個清晰、合理且具有說服力的『判斷標準』與『衡量基礎』。」
在監護權案件中,律師不能只是空洞地告訴法官「我的當事人是個好爸爸/好媽媽」。我們必須提出一個完整的論述框架,例如主張「穩定性原則」對幼兒至關重要,並以此為基礎,論證我方當事人所能提供的生活環境、教養模式如何更能維持孩子的穩定性。我們是在協助法官建立一把「尺」,並用這把尺去衡量案情,最終得出對我方有利的結論。
在分割共有物案件中,律師會提出一個具體的分割方案,並詳細闡述這個方案為何最能兼顧「公平性」與「經濟價值」。我們會引導法官從「如何讓這塊土地發揮最大效用」的視角來思考,而不是陷入「如何讓每個人都滿意」的死胡同。我們提供的不只是一個請求,而是一個完整的決策模型。
可以說,在觀點之爭的戰場上,律師是一位「決策框架的建築師」。我們的工作是建構一個讓法官能夠安心採納、且在判決書中能夠清楚闡述理由的邏輯體系。這不僅僅是為當事人辯護,更是協助司法系統在複雜的人性與利益衝突中,做出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決定。這份價值,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法律條文操作。
這個「事實 vs. 觀點」的思維模型,不僅適用於法庭,更能有效地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幫助我們減少無謂的衝突,開啟更有意義的對話。
當您下次與人發生爭執時,不妨先在心裡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爭的,是事實還是觀點?」
尤其在面對政治、宗教等高度敏感的議題時,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往往只會讓彼此都面紅耳赤,不歡而散。在一個民主社會,觀點的差異是常態,而選舉制度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集體解決觀點之爭的機制。與其浪費時間在無法說服的爭吵上,不如尊重彼此心中都有一把尺,並在可以共同決定的時候,做出自己的選擇。
學會這個區分,能讓您在溝通中更加冷靜、更有策略,避免陷入情緒化的泥淖,將心力專注於真正可以解決的問題上。
從日常生活的抬槓,到法庭上數百萬、數千萬利益的爭奪,許多衝突的根源,都來自於對「事實」與「觀點」的混淆。
本文帶您走過了一趟律師的思維旅程:我們首先釐清了「事實」的可驗證性與「觀點」的主觀性;接著,我們看到這個思維框架如何在法庭上,區分出以「證據」為王的訴訟,以及需要法官進行「價值權衡」的案件;最後,我們理解到,律師在後者所扮演的關鍵角色,正是為法官提供一個足以信賴的「判斷標準」。
這套思維模式,最終回歸到一個核心價值:清晰。
當您能清晰地分辨爭議的本質,您就能在訴訟中找到正確的施力點,與律師進行更有效的溝通。當您能清晰地看見對話的底層結構,您就能在生活中避免無謂的紛擾,建立更和諧的人際關係。
許多人尋求法律協助,是希望得到一個能保護自己的工具。然而,最強大的「法律護身符」,從來不是外在的條文或判決,而是您內在的思維清晰度。能夠冷靜分析、準確判斷、看透問題本質的能力,才是能陪伴您穿越人生各種複雜挑戰的真正力量。而我的工作,正是運用這份專業,協助您在迷霧中,找到那條最清晰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