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JUL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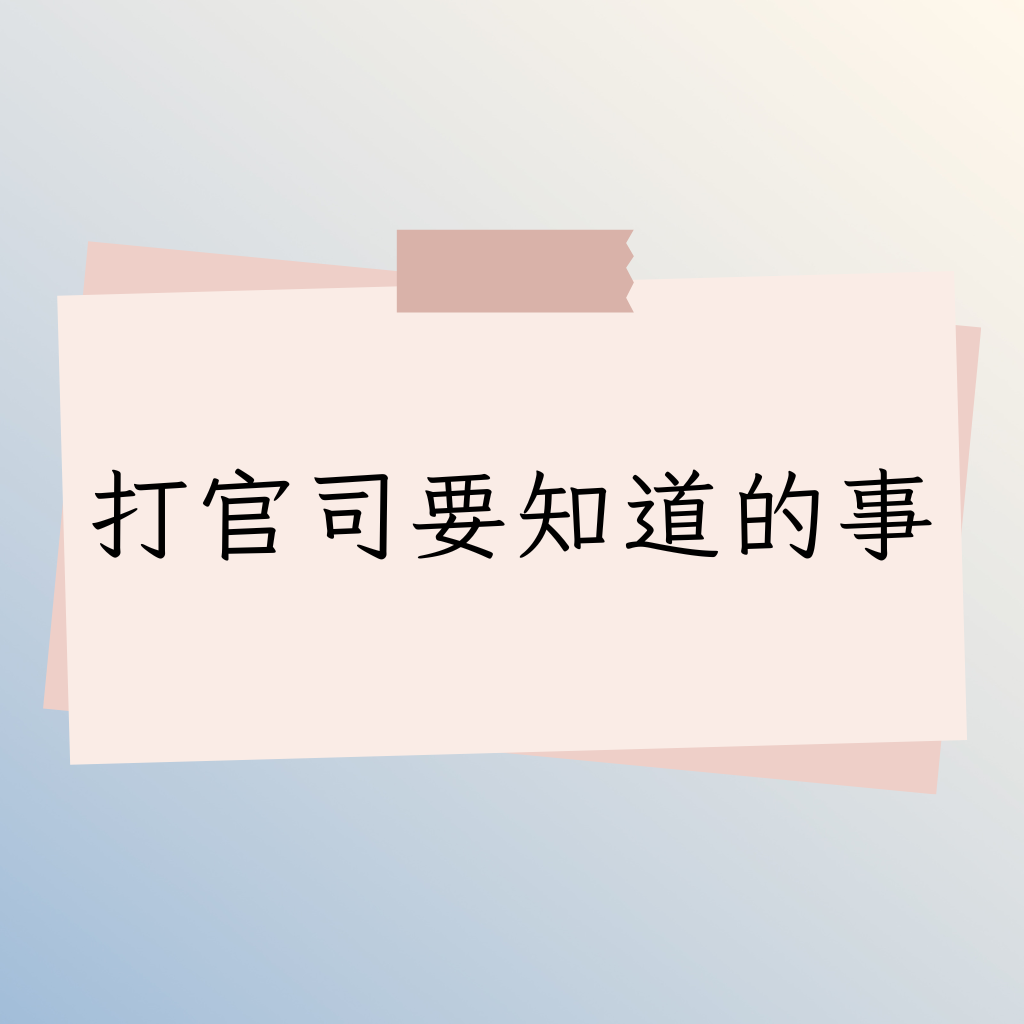
身為律師,工作日常似乎總與「說服」脫不了關係。我們想說服法官、說服檢察官,為當事人的權益奮鬥。但這也讓我時常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溝通中,我們真正需要說服的對象是誰?而哪些人,又是我們「永遠不可能說服的人」?
最近我從不同領域的專家身上得到許多啟發。例如,專職作家吳軍先生,他出身理工科,曾在 Google 和騰訊等頂尖科技公司任職。他分享的「工程師思維」,強調如何將一個龐大的問題,拆解成數個可執行的小單元,再用程式邏輯逐一擊破。
另外,我也關注一位中國大陸的醫師薄世寧先生,他分享的「醫師思維」同樣令我印象深刻。醫師面對主訴「咳嗽」的病人,腦中會浮現從普通感冒、肺炎到肺癌等各種可能性。但醫師不會立刻對每位咳嗽病人都進行最高規格的癌症篩檢,因為這不符合機率原則,也無視檢查的成本與對病人可能造成的不適。他們會依循一套嚴謹的診斷邏輯,在有限的資訊中,透過症狀、經驗與必要的檢查,一步步縮小範圍,找出病灶。
這些跨領域的思維模式,無論是工程的拆解、還是醫學的診斷,其核心都是一套在複雜情況下解決問題的「心法」。這讓我反思,法律工作除了鑽研法條與判決,更重要的是背後那套「法律思維」。我發現,將不同領域的心法內化,對我在辦案、處理法律爭議時,有著極大的助益。
因此,我想透過這篇文章,分享一個從法庭活動中提煉出的核心溝通思維,希望能幫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聰明、更高效地進行溝通。
大家在觀看戲劇或新聞時,可能都看過法庭上律師們唇槍舌戰的場景。但您是否想過,律師們滔滔不絕,究竟是想說服誰?
答案或許和你想的不一樣。
在台灣的法庭上,律師的主要心力,都集中在說服「法官」這位中立的裁判者。無論是民事求償或刑事辯護,我們的目標都是向法官呈現一套對我方當事人最有利的事實與法律解釋。我們從來不抱任何期望,能說服對方的律師或當事人。
這個道理放諸四海皆準。前陣子強尼戴普(Johnny Depp)與前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官司引發全球關注,如果您有留意,會發現美國律師在法庭陳述時,眼神與姿態主要都是朝向「陪審團」。因為在美國的陪審團制度中,真正決定案件走向的,正是這群由素人組成的陪審團,而非僅負責指導訴訟程序的法官。
無論在台灣或美國,律師都清楚一件事:說服的對象,永遠不是與你立場對立的「對手」,而是掌握最終決定權的「第三方」。
對方的律師受其當事人所託,領取酬勞,其職責就是捍衛己方立場,他們不可能被你說服。在法庭這個高張力的場域,任何試圖說服對手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
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法庭智慧,一旦應用到日常生活中,卻能幫助我們看清許多溝通困境的本質。
很多人在生活中,時常陷入一個誤區:沒有搞清楚自己真正要說服的對象是誰,因而將大量的時間與精力,耗費在不可能說服的人身上。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網路上的各種爭執,尤其是政治議題。在社群媒體的新聞貼文底下,時常可見不同立場的網友激烈交鋒。
每當看到這些留言串,我總會思考:留下這些言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假設某甲與某乙在網路上因支持不同政黨而爭論不休。某甲引經據典,自認邏輯清晰、道理充分,希望能「點醒」某乙。但我們幾乎可以預見,這場爭論的結局,絕不會是某乙恍然大悟地回覆:「啊!您說得太有道理了,我過去真是井底之蛙。從今天起,我決定轉而支持您所支持的候選人!」
這種場景在現實中幾乎不可能發生。一個人的政治立場,通常是長期生活經驗、價值觀與同溫層積累的結果,極難因為陌生人的幾則留言而改變。當雙方立場尖銳對立時,爭論的目的早已不是「說服」,而淪為相互指責、甚至是情緒的宣洩。
從溝通策略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場高成本、零回報的互動。你投入了寶貴的時間、專注力與情緒能量,卻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目標。你的言論,既無法說服對手,也很難影響到那些沉默的旁觀者,最終往往只剩下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互相按讚取暖。
當然,凡事有例外。如果你的身分是特定粉絲專頁的小編、或是有意帶動輿論風向的專業人士,你的「爭論」其實是一場表演,目標是影響潛在的第三方讀者,這時的公開辯論便有其策略意義。
但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在投入一場網路論戰前,或許可以先問問自己:我的「法官」是誰?如果這場爭論中沒有值得被說服的第三方,也沒有任何實質利益,那麼,這或許就是一場你該優雅轉身、直接棄權的比賽。
將法庭智慧帶入職場,更能體現其價值。職場上的溝通,往往直接關係到專案成敗、責任歸屬與個人評價。此時,辨識「關鍵第三方」的能力,就成了致勝關鍵。
(一) 當爭論需要被看見:以公司旅遊預算為例
假設公司正在討論員工旅遊的地點與預算,你和同事A的意見相左。你們在公司的LINE群組裡公開討論,你主張提高預算、選擇更優質的方案,而A同事則希望控制成本。
在這種情況下,公開的爭論就是必要的。因為這件事的「法官」,是全體擁有投票權的同事。你的目標不是要說服只有一票的A同事,而是要透過清晰的論述與比較,爭取其他大多數同事的支持。你們的討論過程,就是一場呈現給全體「陪審團」看的公開說明會。此時,若選擇與A同事私訊溝通,反而無法達到影響集體決策的目的。
(二) 當責任需要被釐清:向主管陳述,而非與同事互推
換一個情境。你和同事A共同負責的專案搞砸了,主管要求你們說明原因。你認為是A的疏失,A則反過來指責你。
這時,你的「法官」是誰?是你的主管。
許多人在這種壓力下,會犯下致命的錯誤:急著在主管面前與同事A爭辯、互相推諉,試圖「說服」A承認錯誤。但這恰恰是最無效的做法。你的同事A,在此刻就是你的「訴訟對造」,他不可能被你說服。
聰明的做法是,將你的溝通焦點從同事A身上,轉移到主管身上。你需要思考的是:主管想聽到什麼?
主管要的不是一場難看的爭吵,而是想了解「事情的全貌」以及「如何解決」。你應該做的,是冷靜、有條理地向主管陳述你所認知的事實,提出相關證據,並展現出你願意承擔責任、解決問題的態度。你的陳述,是為了提供資訊給「法官」做判斷,而不是為了跟「對手」吵贏。
這兩種職場情境,完美地詮釋了「你的聽眾,決定你的策略」。當決策權在群體手上,你需要公開的演說與倡議;當決策權在單一權威手上,你需要私下的、理性的、基於事實的彙報。
學會辨識「無法說服的人」,最終會導向一種更深層的智慧:策略性的沉默。
我個人其實不太喜歡在計程車上和司機大哥聊政治。並非不尊重他們的看法,而是從溝通效益上考量,這是一場穩賠不賺的交流。
如果立場相同,不過是互相取暖、罵罵另一方,沒有太多新意;如果立場不同,在一個密閉的車廂內,你一言我一語,氣氛很容易變得尷尬。你不可能在短短20分鐘的車程內改變他數十年的人生信仰,他同樣也說服不了你。
對我而言,這段通勤時間,或許是從一個法院趕往另一個法院途中寶貴的休息空檔,我可以閉目養神,或回覆當事人的訊息。把精力耗費在一場注定沒有結果的爭論上,實在不划算。
因此,我會選擇策略性的沉默。這不是示弱或退讓,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是將有限的個人資源(時間、心力、情緒)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懂得辨識一場不值得打的仗,並選擇不去參與,這本身就是一種力量與智慧的展現。
從法庭到生活,從網路到職場,我們可以將這套「律師的說服思維」歸納為兩大核心心法:
在投入任何一場爭論或溝通前,先評估這場「賽局」的本質。問自己:對方是可能被說服的嗎?這場溝通存在一個擁有決策權、且可能被我影響的「第三方」嗎?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這就是一場無意義的消耗戰。學會辨識並優雅地放手,是保存個人精力的第一步。
一旦確認這是一場值得投入的溝通,下一步就是精準地「鎖定法官」。辨識出誰是真正的決策者——是你的主管、客戶、投票的群眾,還是其他關鍵第三方。然後,將你所有的心力與策略,都用在說服「他」身上。你的論述方式、呈現的證據、溝通的態度,都應該是為這位決策者量身打造的。不要將砲火浪費在你的「對手」身上,那只會讓你的溝通失焦,離目標越來越遠。
希望這套從法律工作中提煉出的思維,能為您帶來一些啟發。如果您對今天的主題有任何想法,或是在您的專業領域(無論是工程、醫學、金融或設計)也有類似的溝通「心法」,都歡迎留言與我分享、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