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JUL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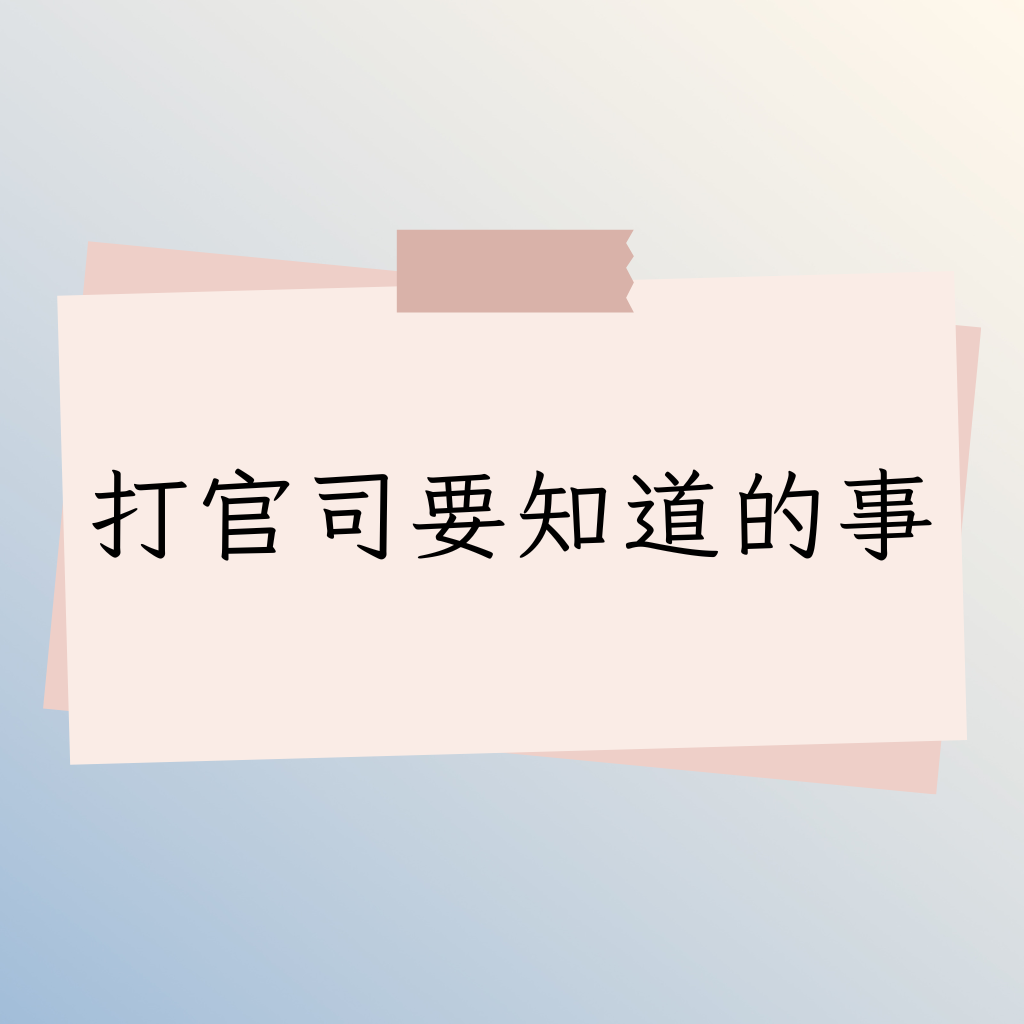
在面對法律糾紛時,許多民眾常有一個疑問:一旦案件進入訴訟程序,甚至判決結果已經出爐,是否就沒有和解的空間了?尤其對於民事案件,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事實上,民事訴訟的和解,展現了極高的彈性,其協商大門幾乎是「隨時」敞開的。
一般民眾對於訴訟的認知,多半停留在「打官司」與「判輸贏」的二元對立。然而,在民事訴訟領域,除了法庭上的攻防,和解始終是解決紛爭的重要途徑。
理解民事和解的彈性,首先需要將其與刑事訴訟的和解機制進行對比。在刑事訴訟中,特別是針對「告訴乃論」之罪,和解或撤回告訴具有較為嚴格的時間限制。例如,告訴的提起必須在六個月內完成,而撤回告訴通常需要在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之。這使得刑事案件的和解,往往伴隨著較大的時間壓力,並在協商談判中成為關鍵的籌碼。
相較之下,民事訴訟的和解則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本質。在民事案件中,當事人「隨時都可以談和解」。這種程序上的高度彈性,反映了民事糾紛的根本目的:彌補損害、恢復平衡,而非單純的懲罰。法律的設計賦予當事人極大的自主空間進行協商,旨在降低訴訟的時間成本、金錢成本與精神壓力,並在某些情況下,有助於維護或修復雙方關係,例如親友或商業夥伴之間的糾紛。這種彈性鼓勵當事人以務實的態度尋求雙贏或損失最小化的方案,而非一味追求判決的「輸贏」。這對於潛在客戶而言,意味著即使官司已進行到一半或判決已下,仍有機會透過和解來「止損」或達成更符合自身利益的結果。
下表進一步比較了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在和解或撤回時機上的主要差異。
判決後仍選擇和解,通常是基於多方面的實務考量,包括案件的金額、標的、爭議複雜度,以及雙方對訴訟結果的風險評估。
促成民事和解的契機,往往與案件的性質息息相關。和解的機會通常與案件的金額或標的較大有關,例如涉及土地、不動產等糾紛。由於這類案件牽涉的利益重大,訴訟所帶來的成本和風險也相對較高,因此雙方當事人往往更傾向於透過和解來控制風險和成本。
此外,即使案件金額不大,但如果爭議點多、證據不明確,或存在法律見解上的歧義,也可能促使雙方考慮和解,以避免冗長且結果不確定的訴訟過程。然而,也有些案件,即使金額龐大,但因涉及情感因素,例如醫療糾紛或與家人生命相關的案件,當事人可能情感投入極深,導致和解的難度大幅增加,更傾向於透過法院判決來尋求一個明確的結果。
(一) 不動產瑕疵糾紛:以海砂屋、漏水屋為例的權利行使
不動產交易是民事糾紛中常見且金額龐大的類型,其和解策略也常因具體情況而異。
1、買方多元權利選擇:減價、損害賠償或解約
當買方購買的房屋出現如漏水屋、海砂屋等重大瑕疵時,法律賦予買方行使「物之瑕疵擔保」的權利。買方可以根據瑕疵的嚴重程度,選擇以下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權利選項是由買方(權利人)來決定行使哪一種,賣方無權強制買方解約。
2、房價波動如何影響和解策略
不動產糾紛的和解策略,有時會受到市場經濟因素的顯著影響。例如,若案件審理期間房價大幅上漲,原本1200萬元的房子可能翻倍至2000多萬元。此時,即使房屋有瑕疵,買方也可能不願解約,因為解約後難以再以原價購得同等價值的房屋。他們會更傾向於要求減少價金或損害賠償,以保留房屋並獲得補償。反之,賣方在房價上漲時,反而可能希望解約,將房屋收回後以更高價格出售,但這必須尊重買方的權利選擇。這顯示了市場因素在法律糾紛和解中的重要影響,也考驗著當事人與律師在策略制定上的靈活性。
和解的契機不僅是時間點,更是雙方對訴訟結果的「風險評估」與「預期落差」逐漸收斂的過程。在訴訟初期,雙方可能對勝訴抱有較高期望,或對自身立場過於自信,導致和解破裂。然而,隨著訴訟的推進,證據的揭示、法官態度的暗示,甚至一審判決的結果,都會讓雙方對案件的「勝算」和「風險」有更清晰的認識。當預期與現實出現落差,或訴訟成本(時間、金錢、精神)累積到一定程度時,和解的機會便會浮現。這意味著在推動和解時,不僅要考慮時間點,更要引導當事人進行務實的風險評估,促使雙方預期收斂,才能真正促成和解。
(一) 訴訟各階段的和解機會與法院調解機制
和解的機會貫穿於訴訟的各個階段:
(二) 小額案件與重大案件的和解考量差異
案件的性質也會影響和解的可能性:
有時,訴訟策略上會採取「以戰逼合」的方式。這不僅是一種策略,更是對人性與社會現實的深刻理解。對於某些態度強硬的對方,訴訟的提起本身就是一種「強制力」的展現,迫使對方正視問題,並將其拉回談判桌。這種策略的深層含義是,在某些情況下,法律程序並非單純的「解決方案」,而是一種「工具」,用來創造談判的壓力與平台,促使原本不願溝通或不負責任的一方,不得不面對並尋求解決。這也說明了,有時訴訟是必要的「手段」,而非最終「目的」。
在民事訴訟中,和解不僅僅是程序的選擇,更是一門藝術,涉及對時機、對方心理和自身籌碼的精準判斷。
和解策略的選擇(主動或被動)是基於對「對方心理」和「案件證據強度」的綜合判斷。有些當事人擔心主動提出和解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有求於他」,從而處於劣勢。因此,他們可能選擇等待對方先提出和解,或在對方未加碼前不予回應,甚至堅持「上法院再說」。這說明和解策略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高度依賴於對對方當事人性格、行為模式的預判,以及自身案件證據的強弱。如果證據確鑿,勝訴機率高,則可以採取較為強勢或被動的策略,讓對方感受到壓力後主動求和。反之,如果證據薄弱或訴訟風險高,則可能需要更積極地尋求和解。
判決結果,特別是一審判決,往往是重要的和解契機。勝訴方可以利用判決結果作為談判籌碼,促使對方考慮和解,避免上訴。例如,勝訴方可以說:「一審法官都已經支持我了,你還要不要談?」。敗訴方則可能因判決壓力而更願意協商,因為他們意識到上訴的勝算可能不高。
對於態度強硬、不認為自己有錯的對方,適時提起訴訟。透過法院的介入與強制力,反而能促使對方正視問題,回到談判桌。此時,訴訟本身成為一種有效的溝通與協商工具。這也表示:訴訟不僅是解決爭議的途徑,更是一種「溝通工具」。訴訟雖然也是一種不得不的方法但上了法院也不代表一定要打到底,很多時候可以彈性運用這個攻跟防這兩個策略。
和解的最終目標並非追求一方全贏或全輸,而是尋求一個「不怎麼滿意,但是都能夠接受」的平衡點。這意味著雙方都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讓步,以達成共識。若雙方都堅持不退讓或不願意讓步,最終只能交由法院判決。然而,法院的判決結果往往是二選一,不見得能完全符合任何一方的期待,且可能導致更漫長的訴訟程序。因此,在許多情況下,和解是更有效率且能為雙方帶來可預期結果的解決方案。
面對複雜的民事訴訟程序和和解策略,律師扮演著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律師的核心價值在於彌補當事人與司法體系之間巨大的「資訊不對稱」,並在過程中給予情緒引導。普通民眾對法律程序、規則、潛在風險一無所知,容易在訴訟中感到無助和迷茫。律師的存在,正是為了提供專業知識,讓當事人能夠「把握節奏與流程」,從被動變為主動。此外,律師還能作為理性的第三方,幫助當事人管理訴訟過程中的情緒(如憤怒、不甘),引導他們從「給對方一個教訓」的衝動,轉向「實現自身權益最大化」的務實目標,這對於促成和解尤其關鍵。
民事訴訟程序複雜,包含準備程序、言詞辯論程序、證據調查等環節。一般民眾不熟悉這些流程,容易在訴訟中感到迷茫,甚至「處處受制於人」。律師能夠幫助當事人理解訴訟的每一個階段,預判可能的發展,並在關鍵時刻提供專業建議,例如何時提出證據、何時應對對方的攻防,甚至如何利用程序上的彈性來促成和解。律師的協助能讓當事人「用比較積極或者說比較有整體觀的態度來去打一個訴訟」。
有些當事人可能僅憑一時氣憤決定訴訟,卻不了解訴訟的長期性、複雜性及潛在風險。律師能提供客觀評估,避免當事人盲目投入,並協助其「把握整個案子的節奏跟流程」。
律師不僅是法律專家,更是「風險管理者」和「策略夥伴」。這說明律師的角色遠不止於法庭上的辯護或書狀的撰寫。更重要的是,律師能夠基於對法律、證據、對方心理的綜合判斷,為客戶提供全面的風險評估和策略規劃。他們幫助客戶在「訴訟到底」和「適時和解」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並在和解過程中,利用其專業知識和談判技巧,為客戶爭取最佳條件。
律師能協助當事人評估案件的勝訴機率、潛在風險、訴訟成本(時間、金錢、精神),並分析各種和解方案的利弊。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和當事人需求,律師能建議是「戰」還是「和」,以及採取主動還是被動的和解策略。作為專業中介者,律師能夠在和解談判中保持客觀,有效溝通,避免當事人因情緒化而錯失和解良機,或在談判中處於劣勢。和解條件的達成,最終取決於雙方是否「你情我願」地接受條件及「整個局勢對您是不是有利,整個證據是不是對您有利」。律師能精準分析證據,判斷案件走向,從而為當事人爭取最有利的和解條件。
民事訴訟的和解,確實具有極高的彈性。從案件尚未進入法院程序,到訴訟進行中的各個審級,乃至於判決結果出爐後,甚至進入強制執行階段,雙方當事人都有機會透過和解來終結紛爭。這打破了一般人對於「判決後就無法和解」的迷思。
和解的達成,最終取決於雙方是否能「你情我願」地接受條件,這與案件的證據強度及整體局勢是否對當事人有利息息相關。訴訟並非總是唯一的解決途徑,有時它更是促成和解的策略性工具,透過法院的介入來創造談判的壓力與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