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JUL 2025 張倍齊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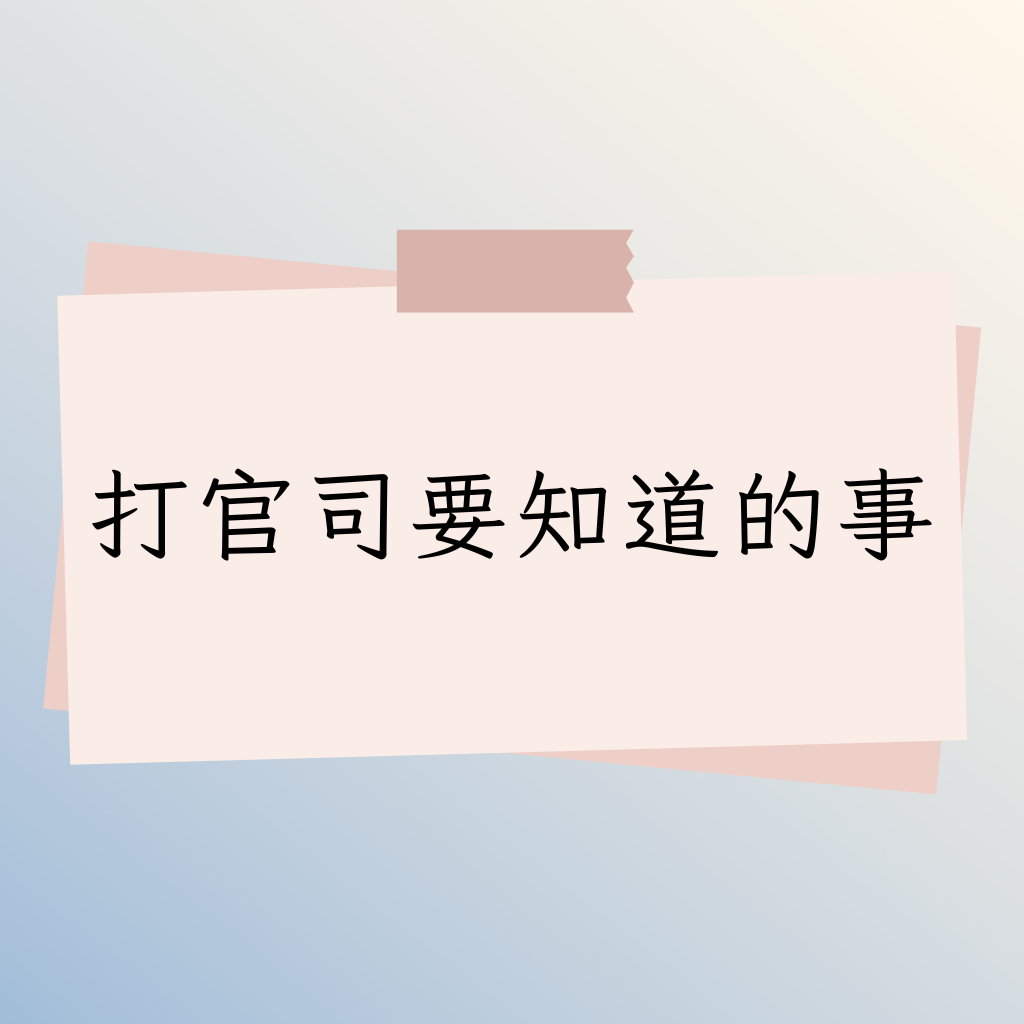
許多當事人在尋求法律協助時,常懷抱著一種期待:「我的證據這麼明確,這個官司應該穩贏了吧?」這份自信,源於對自身所掌握事實的堅信不移。然而,訴訟的真實樣貌,遠比我們想像的複雜。它並非像電影《葉問》中,主角獨自對著木人樁練習詠春拳那樣,對手會靜止不動,任由您攻擊。
在真實的訴訟戰場上,您的對造——無論是民事案件的被告,還是刑事案件的另一方——是一個活生生、會思考、會反擊的個體。他(她)不會躺在那裡任您攻擊,更不會對您的主張全盤接受。這就是訴訟的核心挑戰:您面對的不是一個固定的靶子,而是一個會閃躲、會格擋,甚至會發動猛烈反擊的對手。
當事人常有的迷思是,只要將手上的「鐵證」呈給法官,法官就會明察秋毫,案件便能迎刃而解。但這種想法忽略了訴訟的「動態攻防」本質。一場官司更像一盤棋局,例如圍棋,您下的每一手棋,都必須預判對手接下來可能的應對,甚至要推演到後續好幾步的變化。僅僅專注於自己手上的棋子有多好,而忽略對手的佈局與反制,往往是導致局勢逆轉的開端。
「張律師,這份對話紀錄寫得這麼清楚,為什麼您還說可能有爭議?」、「這個合約白紙黑字,對方怎麼可能賴得掉?」這是律師在執業過程中,經常聽到的疑問。當事人往往因為身處其中,對自己掌握的證據抱持著極大的情感投入與樂觀預期。然而,律師的職責,恰恰是扮演那個潑冷水的「風險管理者」。
這就好比一位外科醫生在術前向病人解釋風險。醫生絕不會只說「這個手術很簡單」,而是會詳盡告知手術的成功率、可能的併發症、術後恢復的挑戰等。即便病人可能體質良好,屬於那95%會成功康復的族群,醫生仍有責任告知那5%的風險。這不是在唱衰,而是專業與盡責的表現。
同樣地,律師的職責就是對您的案件進行「壓力測試」。當您提出一份證據時,律師的腦中會立刻啟動「風險雷達」,從兩個關鍵角度進行檢視:
1.法官會怎麼看? 法官是否會全然採信這份證據?它的證明力有多強?是否存在其他解釋的空間?
2.對方會怎麼說? 這才是更關鍵的一點。對方律師會如何攻擊這份證據的有效性?他們會不會提出反證?
律師的「悲觀」或「質疑」,並非不信任當事人,而是一種必要的專業服務。正是透過這種反覆的質疑與推演,我們才能在真正踏上法庭前,找出案件的潛在弱點,並預先建立防禦工事,避免在法庭上被對手突襲而措手不及。這種事前演練,是將您的案件從「自認的強大」淬鍊成「經得起考驗的強大」的必經過程。
訴訟攻防的核心,往往不在於誰擁有單一的「真相」,而在於誰能說服法官相信自己的「敘事版本」更具說服力。對手的目標不僅僅是駁斥您的證據,更是要將您的證據納入他們的故事框架中,使其失去原有的意義,甚至反過來對您造成傷害。
以常見的LINE對話截圖為例。假設您(原告)提出一段對話,證明與房客(被告)已合意終止租約,要求對方返還房屋。您可能認為這已是鐵證。然而,被告的反擊可能超乎您的想像:
在這個「釜底抽薪」的策略下,您提出的「終止合意」證據並未被推翻,但它的意義被徹底改變了。它從「契約的終點」變成了「一段被新合意所取代的舊歷史」。法官評估的,就不再是單一事實的真偽,而是兩段相互競爭的敘事,哪一個更為可信。這也揭示了訴訟的殘酷現實:掌握敘事權的一方,往往就能掌握勝敗的走向。
為了讓您更清晰地理解這種思維上的差距,以下表格整理了當事人的主觀視角與訴訟現實的攻防情境:
| 您的主觀想法 | 對造的可能攻擊角度 | 律師的策略性應對 |
|---|---|---|
| 「這份LINE截圖證明他欠我錢。」 |
1. 否認對話真實性,主張偽造。 2. 承認對話,但辯稱這是玩笑話。 3. 指出後續已有清償行為,或有其他債務可抵銷。 |
1. 準備好驗證對話真實性的方法。 2. 結合前後文與其他佐證(如匯款紀錄),證明借貸關係。 3. 預先調查對方可能的抵銷主張,並準備反駁證據。 |
| 「這封Email寫明了合約條件,他賴不掉。」 |
1. 主張Email僅為初步討論,非最終合意。 2. 提出後續的會議紀錄或通話內容,證明Email條件已被修改。 3. 辯稱其後續行為與Email內容不符,證明雙方無意受其拘束。 |
1. 找出其他能佐證此Email為「最終版本」的證據。 2. 證明我方已依Email條件履行義務,而對方亦曾受益。 3. 盤點所有後續溝通,確認無不利我方的變動。 |
| 「我有驗傷單,可以證明他家暴。」 |
1. 承認有肢體衝突,但主張是雙方互毆,對方傷勢更重。 2. 辯稱是對方先言語羞辱或挑釁,自己是出於防衛。 3. 主張傷勢是對方自己不小心造成的,與自己無關。 |
1. 除了驗傷單,蒐集其他證據(如錄音、證人、報警紀錄)還原事件全貌。 2. 證明對方長期的精神虐待與控制行為,建立其施暴者的形象。 3. 預判對方可能的人格抹黑,並準備好澄清的證據。 |
離婚訴訟,是將前述理論體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戰場之一。因為夫妻雙方最了解彼此的弱點,攻防也因此格外激烈。讓我們以一個常見的案例,進行一場紙上推演。
假設您是原告,決定以民法第1052條第2項「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為由訴請離婚。您的起訴狀主張,雙方因價值觀長期不合,經常爭吵,且已分居超過兩年,感情名存實亡,婚姻已生破綻。從您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事實,理由正當。
在遞出訴狀的那一刻,木人樁的幻想就該結束了。我們必須立刻切換到棋手的思維模式,開始預判:當被告收到這份訴狀時,他(她)會有什麼反應?
面對您的起訴,被告最有可能的策略,就是徹底顛覆您的「受害者」敘事,將您塑造成婚姻破裂的「加害者」。他可能會向法官提出如下答辯:
「法官大人,我承認我們確實分居了,但分居的原因,是原告自己外遇在先,並擅自離家出走!我們的感情本來很好,是他(她)的背叛才導致婚姻出現問題。他(她)現在還惡人先告狀,想把離婚的責任推到我身上。」
這是一常見的反擊。因為它引入了離婚訴訟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法律概念:「可歸責性」。法院在審理這類離婚案件時,有一個重要的實務見解:對於婚姻破裂「可歸責程度較重」的一方,原則上不能主動訴請離婚。白話來說,就是「誰犯的錯比較大,誰就沒資格提離婚」。
一旦被告成功地將「外遇」、「拋家棄子」的標籤貼在您身上,整個訴訟的焦點就會從「婚姻是否無法維持」,轉移到「是誰造成婚姻無法維持」。法官的天平開始傾斜,您從一個尋求脫離痛苦婚姻的原告,瞬間變成了需要為自己行為辯解的被告。對方會乘勝追擊,羅列您過去種種不是,例如不分擔家務、羞辱謾罵、對家庭沒有貢獻等,目的就是要證明您的「可歸責性」遠大於他。若此策略成功,法院很可能會判決駁回您的離婚請求。
這也給所有考慮提起訴訟的人一個最深刻的警示:當您決定按下提告按鈕時,您不只是將對方置於法庭的檢視之下,更是將您自己的人生與行為,攤開在法官的顯微鏡下,接受最嚴格的審視。
面對對方可預見的猛烈攻擊,一位有經驗的律師不會等到對方出招後才倉促應對,而是在起訴前就已經「超前部署」。這需要建立在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絕對的信任與坦誠之上。
您必須向律師坦承自己所有可能的弱點。例如,如果您確實與同事有超越友誼的互動,即便您不認為是外遇,也必須告知律師,因為對方很可能會以此大作文章。您的坦誠,不是給自己挖坑,而是給律師打造最強盾牌的原料。
基於這些資訊,律師可以擬定多層次的防禦策略:
1.先發制人(打預防針): 與其被動等待對方指控,不如在第一份書狀中就主動出擊,進行「策略性消毒」。例如,我們可以這樣寫:「被告長期以來對原告的工作與正常社交抱持無理猜忌,動輒以不實言詞指控原告與同事有染,造成原告巨大精神壓力,此亦為雙方婚姻難以維繫之原因。」這招「打預防針」,能預先設定議題框架,將對方可預期的攻擊,轉化為證明其「無理取鬧」的證據。
2.分批提出證據: 我們不必在第一份書狀中就打出所有手上的牌。先提出基本主張,觀察對方的答辯內容,再針對其弱點,提出第二波、第三波的證據,層層進逼,掌握訴訟節奏。
3.擬定和解與訴訟雙軌策略: 在備戰的同時,也要思考和談的底線。我們是想速戰速決,還是有長期抗戰的準備?在財產分配、子女監護權或扶養費上,我們的讓步底線在哪裡?清晰的策略目標,能讓我們在訴訟與談判之間靈活切換,尋求最大利益。
當然,沒有人能像神算一樣預測到戰場上的所有突發狀況。但越是周全的準備,越能讓我們在面對意外時保持冷靜,不至於陣腳大亂,倉促尋找證據。
從將對手視為「木人樁」的誤解,到理解訴訟是一場複雜的「攻防棋局」,這趟思維的轉變,是每一位當事人走向成功解決紛爭的必經之路。您的對手不僅會反擊,甚至可能將您打得焦頭爛額。
因此,在提起任何訴訟前,務必與您的律師進行深入且坦誠的溝通,仔細盤點自己手中的武器,並預判對方可能的回應。我們要思考的,不只是「我能證明什麼」,更是「當我證明了A,對方會如何用B來反駁,而我該如何用C來回應B」。
最後,必須強調一個最重要的觀念:萬全的訴訟準備,其最終目的,不一定是在法庭上擊倒對方。
當您透過律師的協助,準備了充分的資料,建立了強大的攻防論述,對方以及對方的律師會清楚地意識到,若將官司打到底,他們勝訴的機率相當渺茫。在這種壓力下,對方主動尋求和解的可能性將會大幅提高。一個準備充分的訴訟策略,本身就是最強大的談判籌碼。它讓您無論是選擇在法庭上奮戰到底,還是坐上談判桌,都能處於更有利的位置,最終達成您真正的目的——無論是透過判決還是和解,都能以對您最有利的方式,解決紛爭,繼續前行。